新(xīn)聞動态
News
潘恒生訪談 :我不覺得周星馳是大家所說的那樣
發布時間:2014-10-20 閱讀量:1787
潘恒生,香港電(diàn)影攝影師協會HKSC會員, 亞洲首屈一指的金牌攝影師。最早與香港電(diàn)影新(xīn)浪潮導演嚴浩合作(zuò)《似水流年》《滾滾紅塵》,金馬金像攝影大成之作(zuò)《阮玲玉》關錦鵬導演,同吳宇森拍攝的《縱橫四海》、還有(yǒu)與徐克合作(zuò)的《倩女幽魂》。潘恒生也是一大批無厘頭電(diàn)影的掌鏡人,從《大話西遊》到《功夫》和《長(cháng)江七号》,星爺的成功也同樣離不開他(tā)多(duō)變的影像。近期作(zuò)品有(yǒu)《霍元甲》《葉問2》《月滿軒尼詩》,全智賢主演好萊塢大片《小(xiǎo)夜刀(dāo)》。

潘恒生的電(diàn)影人生
問:首先您是名(míng)電(diàn)影攝影師,也做導演,同時也是演員,然後您還是浸會大學(xué)的老師。在這麽衆多(duō)的身份當中(zhōng),您覺得電(diàn)影攝影師在您的生命中(zhōng),它到底是什麽樣的一個地位?
答(dá):我覺得我是個電(diàn)影人,電(diàn)影人就是一生都在電(diàn)影裏面工(gōng)作(zuò)。大學(xué)畢業後我是到電(diàn)視台工(gōng)作(zuò),我是攝影師,當時的我就準備投身到電(diàn)影這個行業裏。在電(diàn)視台我們還是拍菲林的,菲林的好處是你對曝光要非常準确,因為(wèi)比方說5.6光圈,要是over了,曝光過了,那後期沒有(yǒu)辦(bàn)法彌補的,這就讓我們對布光的要求有(yǒu)一個長(cháng)時間的鍛煉,這是成為(wèi)電(diàn)影人的準備功夫吧。
關于當演員,這麽多(duō)年的電(diàn)影工(gōng)作(zuò),普通觀衆隻認識我是演員。我為(wèi)什麽當了演員了呢(ne)?就是我在攝影的過程裏面,那時候香港是沒有(yǒu)打光替身的,你不能(néng)叫演員出來打光,讓演員走位給你看。通常是攝影組的人走位,因為(wèi)燈光組的人要打燈,有(yǒu)工(gōng)作(zuò)。可(kě)是這些人是有(yǒu)攝影工(gōng)作(zuò),你不能(néng)怪他(tā),他(tā)沒投入到電(diàn)影裏面,所以他(tā)光站在那邊打。但是演員出來的時候他(tā)是有(yǒu)情緒的,所以他(tā)演戲可(kě)能(néng)頭轉來轉去,結果所有(yǒu)打的燈都照不到臉上,沒有(yǒu)氣氛。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,我比較熟悉劇情,很(hěn)多(duō)時候我就走一遍給燈光師打,根據那個戲的情緒做動作(zuò)。這個過程中(zhōng),導演就會在監視器前看你看你怎麽演戲,有(yǒu)的說這個戲不錯,就找你演。大部分(fēn)街(jiē)道上的普通觀衆就覺得我是個演員,從來不叫我是個攝影師,其實是工(gōng)作(zuò)上的需要變成一個演員。
而攝影這一部分(fēn)的工(gōng)作(zuò)直到2010年,工(gōng)作(zuò)時間比較空閑一點,跟卓伯棠,他(tā)是博士,搞正規電(diàn)影學(xué)習設計總監,跟他(tā)碰過我幾次。然後就邀請我到他(tā)們學(xué)校,說是時候要回饋給學(xué)校。當攝影師以後空閑的時間一直定不下來,因為(wèi)教書要定下時間。2010年我比較空閑一些,又(yòu)經不起他(tā)這麽多(duō)次找我,就開始跑到浸會裏面開始教書,傳承一下。還是因為(wèi)這麽多(duō)年在電(diàn)影圈的生涯,也有(yǒu)點經驗,跟小(xiǎo)朋友講一下。主要我覺得講的不是技(jì )巧性的東西,尤其是現在數碼變更得很(hěn)快。我能(néng)給學(xué)生的是方向性的東西,因為(wèi)畢竟我在片場、在電(diàn)影圈這麽多(duō)年的生活,知道怎麽可(kě)以生存,應該注意什麽,我希望把這些東西給年輕人,就是有(yǒu)勵志(zhì)在這個電(diàn)影行業發展的人一點經驗的啓示,讓他(tā)們不要多(duō)走冤枉路。我覺得我是個電(diàn)影人,電(diàn)影人其實是離不開的電(diàn)影,不管是教書,還是做電(diàn)影攝影師,都是在一個世界裏面。
潘恒生的電(diàn)影思維

《小(xiǎo)夜刀(dāo)》劇照
問:我之前看過一篇文(wén)章說我們這一代所謂的青年影迷都是受電(diàn)視的影響比較深,我們從小(xiǎo)都是看電(diàn)視或者是吃着爆米花(huā)看着美國(guó)大片出來的。所以我們的電(diàn)影思維比較差。那作(zuò)為(wèi)一個電(diàn)影攝影師來說,究竟什麽是個大熒幕的思維?
答(dá):我覺得最簡單的講法,因為(wèi)我出身也是電(diàn)視台的攝影師,當年我也是拍了很(hěn)多(duō)電(diàn)視劇的東西,用(yòng)的也是菲林,它非常接近電(diàn)影的表現手法。到我出來拍電(diàn)影的時候,我有(yǒu)一部戲叫《生死線(xiàn)》,這個戲是梁普智導演的,他(tā)原來是一個拍廣告的。你知道廣告是對攝影非常講究,因為(wèi)廣告在香港來講隻有(yǒu)30秒(miǎo),所以一個鏡頭裏面要講很(hěn)多(duō)東西,非常講究角度,拍什麽東西,光線(xiàn),大小(xiǎo)。他(tā)一直都是這種導演,所以他(tā)對這個電(diàn)影攝影要求非常高,特别能(néng)用(yòng)鏡頭講故事。他(tā)很(hěn)多(duō)次都問我,怎麽設計那個鏡頭,問我這場戲今天怎麽拍,那我就想搖一個吧,從A搖到B,軌道推進去。那時候劇本不是那麽全的,拍一場我就來看哪一場的劇本,所以這個戲當然是導演最清楚,然後他(tā)就根據我的建議,從戲裏面想,就說有(yǒu)點不對,好像不是A拍到B啊,是從B拉出來,看到AB兩個人才對。那好吧,導演都這麽說了。後來他(tā)又(yòu)問了,這個鏡頭怎麽設計?我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當然是要給他(tā)答(dá)案選擇,我就說兩個人推近一個人。他(tā)就想,是應該一個人拉出來,他(tā)老是這樣改我的鏡頭我生氣了,這又(yòu)不是我的工(gōng)作(zuò)。你要我提供想法你不能(néng)批評我,年輕人嘛,就這樣。
後來有(yǒu)一個鏡頭,我們在《生死線(xiàn)》裏面有(yǒu)一個湖(hú),中(zhōng)間有(yǒu)個樹,戲裏面有(yǒu)個壞人挂在樹上面。他(tā)就問我,這個鏡頭應該怎麽拍?我就說開始從兩個身上,然後一直拉到全景看到整個湖(hú)中(zhōng)間有(yǒu)棵樹上面人在上面,這樣的鏡頭蠻厲害的。他(tā)就想,這個不對啊,這個鏡頭不是電(diàn)影鏡頭,什麽是電(diàn)影鏡頭,講故事嘛,要讓觀衆非常感動,因為(wèi)觀衆是付錢看電(diàn)影的,你老是想這種電(diàn)視的鏡頭。電(diàn)視上面觀衆沒要求的,他(tā)不用(yòng)付款,不喜歡他(tā)不會說話的。可(kě)是到戲院裏面他(tā)付錢,看到這種電(diàn)視的鏡頭他(tā)不如回家看電(diàn)視。那個時候我生氣是因為(wèi)你叫我講就講,你批評我幹嘛。可(kě)是這話就說出電(diàn)視和電(diàn)影鏡頭的分(fēn)别,戲院裏看觀衆要有(yǒu)滿足感,他(tā)付錢是有(yǒu)要求的。電(diàn)影人講鏡頭不能(néng)說随随便便把故事講出來就夠了,必須要有(yǒu)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驚喜,讓觀衆覺得滿足,這才是電(diàn)影的鏡頭。所以這話在我的電(diàn)影生涯裏面影響非常大,就是每當想随便拍個鏡頭,這個句話就會提醒我,觀衆是付錢的來看這個鏡頭的,不能(néng)馬虎,必須用(yòng)心設計,讓觀衆得到滿足,這才是電(diàn)影人,這個鏡頭才是講故事,電(diàn)影不管是鏡頭、内容、演戲、後台都要講究。從這個事情我學(xué)到了很(hěn)多(duō)。
從《似水流年》到《阮玲玉》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 (斯琴高娃 / 顧美華)(DP 潘恒生 HKSC)
問:潘老師,您是香港電(diàn)影新(xīn)浪潮的領頭人,當年和嚴浩先生合作(zuò)的《似水流年》讓我們都印象十分(fēn)深刻,裏面那個舒緩的鏡頭真的特别特别柔美。到包括後來金像獎最佳攝影師《阮玲玉》,這部電(diàn)影有(yǒu)很(hěn)多(duō)影迷,有(yǒu)一年電(diàn)影資料館還放膠片版,就是菲林版,觀看的人非常的多(duō)。那應該是您年輕的時候一個創作(zuò)初期,您能(néng)不能(néng)跟大家分(fēn)享一下對這種新(xīn)事物(wù)的接受和您當時創作(zuò)的心境,對電(diàn)影的觀念。
答(dá):《似水流年》其實算是我第二部電(diàn)影,第一部電(diàn)影是《我為(wèi)你狂》,金炳興當導演,他(tā)是一個很(hěn)出名(míng)的編劇當導演,可(kě)惜這部戲我沒能(néng)夠完成。當時我還在電(diàn)視台工(gōng)作(zuò),然後被請去就拍《似水流年》,《似水流年》算是第一部從香港到大陸來拍的電(diàn)影。那時候82、83年,我們年輕,經驗也不多(duō),拍攝的時候廣州我們也去過,北京上海我們也去過,一直到汕頭那個地方,那裏很(hěn)有(yǒu)農村的感覺。
我們到那個農村導演就說這是從明朝開始保留的原貌,沒有(yǒu)改變過,特别幸運。當時我們因為(wèi)年輕,看那個地方唯一的感覺就是很(hěn)有(yǒu)生命力,牲畜都跟路上的泥土混在一起。我們香港比較講究潔癖,可(kě)是沒辦(bàn)法,整天鞋子上都是泥和糞便,這種生活給住在樓層的人有(yǒu)非常驚喜和震撼的感覺。《似水流年》的時候我們剛從電(diàn)視台出來,突然變成拍電(diàn)影。我們就重新(xīn)要學(xué),重新(xīn)要歸納我們懂的東西到新(xīn)的平台上去。雖然那個電(diàn)影是個文(wén)藝片,比較容易操控,但是在曝光方面,對我來講,是要重新(xīn)看整個畫面的曝光,是不是都在菲林的寬銀幕裏面,怎麽表現出來。我覺得這是我離開香港一個本土的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的适應能(néng)力發揮出來的一種應變能(néng)力。

《阮玲玉》劇照
到拍《阮玲玉》比較成熟了。《阮玲玉》也是到大陸來拍,90年的時候。大陸經濟開發差不多(duō)可(kě)以了。我們那時候到上海,那裏是個繁華的都市,有(yǒu)新(xīn)的東西,也有(yǒu)蠻舊的,像上個世紀的弄堂,是1920年遺留下來的一種文(wén)化沉澱。在拍《阮玲玉》很(hěn)多(duō)時候用(yòng)的是很(hěn)舊的景,現在可(kě)能(néng)已經拆掉了。那時候我們看那個景都是1920年、1930年的,特别生活,特别文(wén)化的一種感覺。《阮玲玉》特别要提的是美術指導配合非常好。老實說攝影其實是拍一個東西,所以沒有(yǒu)美景,沒有(yǒu)漂亮的演員,沒有(yǒu)漂亮的服裝(zhuāng),你那個攝影不可(kě)能(néng)特别漂亮的,超越别人的。那個時候我是覺得,第一,很(hěn)多(duō)很(hěn)懷舊很(hěn)有(yǒu)風味的景我們可(kě)以拍,另外就是美術要做好。舉例就是阮玲玉住的那個地方,其實我們就在她住的不多(duō)遠(yuǎn)的地方拍,那個床原來擺着的。美術指導找出那個年代的衣服,叫美術學(xué)院的學(xué)生照着衣服上的圖案畫出來。影片裏那個商(shāng)場都是畫出來的,他(tā)們花(huā)了一個月的時間畫到牆上面。本來我們跟這個地方的房東講,這個樓借三個月給我們拍,然後屋主說你們是要還原白牆的。最後看到我們這麽漂亮的房間他(tā)就不用(yòng)還原了,太漂亮了,就保留這個。

《阮玲玉》劇照
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拍《阮玲玉》的時候我們用(yòng)光突出人物(wù),景跟人物(wù)的光的反差對比比較大。我們在拍的時候就盡量把反差控制,光打人就打人,就不會掉到牆上面,不會擋住這樣。然後加上美術,加上這個服裝(zhuāng)和發型,這個環境,這個人物(wù)定位就特别準。我覺得這整體(tǐ)的配合就變成這個電(diàn)影。《似水流年》和《阮玲玉》兩部電(diàn)影,《阮玲玉》運動比較多(duō),《似水流年》運動比較少。兩個戲的拍攝的環境、拍攝的條件都給我非常充分(fēn)的攝影發揮機會。
你覺得我有(yǒu)攝影風格?

《大話西遊》劇照
問:您之前拍文(wén)藝片比較多(duō),到後來您又(yòu)拍出來像《縱橫四海》、《大話西遊》、《功夫》、《長(cháng)江七号》,這一系列在商(shāng)業史上既叫好又(yòu)叫座的片子。這就感覺跟您的多(duō)重身份一樣,我們知道您既在藝術片運境上面有(yǒu)一定的見解,又(yòu)在商(shāng)業片中(zhōng)又(yòu)遊刃有(yǒu)餘,所以您是怎麽看待自己的攝影風格的呢(ne)?
答(dá):因為(wèi)我當攝影師這麽多(duō)年,一年接兩部戲,我不喜歡有(yǒu)戲重疊的。有(yǒu)些人是一部戲拍得差不多(duō),他(tā)就又(yòu)接另一部戲,然後叫人家頂最後幾天。我不習慣,我習慣一部戲完結了,再接另外一部戲。我是比較少産(chǎn)的攝影師。我從來不看自己是什麽風格的。我記得很(hěn)久以前有(yǒu)個雜志(zhì)訪問就問這個問題:潘先生您攝影的風格是什麽?我說:你覺得我有(yǒu)攝影風格?那你告訴我,我的風格是什麽?然後他(tā)舉個例子,有(yǒu)一部戲他(tā)問那個導演:這個戲是不是第一場戲是潘恒生攝影的,之後就沒有(yǒu)他(tā)了,确實是這樣!因為(wèi)我沒有(yǒu)接這個戲,他(tā)要補戲的時候找我,去補了一場。我問他(tā)怎麽知道,他(tā)說是因為(wèi)我那個風格是很(hěn)多(duō)軌道走動的。我為(wèi)什麽喜歡用(yòng)軌道,因為(wèi)我覺得電(diàn)影是兩維的東西,觀衆投入到兩維的世界裏面。電(diàn)影好玩的地方是把觀衆帶進那個立體(tǐ)的世界裏面,好像旅遊一樣,你進來看看,左看看右看看前面看看後面,這樣從兩維變成三維空間的感覺要用(yòng)軌道帶出來,改變那個視覺視點,變成整個世界是立體(tǐ)的,這樣講出來的故事才能(néng)讓觀衆感同身受。這是我常用(yòng)軌道的原因。其實拍每一部電(diàn)影都是我看了劇本,跟導演溝通以後就投入到故事裏面。每一個電(diàn)影故事它有(yǒu)不同需要,我就盡我所能(néng)去滿足。我沒有(yǒu)預定我要拍文(wén)藝片,然後準備拍動作(zuò)片,然後準備拍商(shāng)業片。我是比較随意的那種,是機遇讓我變成這個樣。

《佛萊迪大戰傑森》劇照
電(diàn)影的人員分(fēn)工(gōng)是很(hěn)清楚,因為(wèi)這是商(shāng)業的行為(wèi)。攝影就隻顧攝影的東西,燈光就顧燈光的部分(fēn),有(yǒu)的攝影師比較被動,他(tā)不能(néng)靠自己能(néng)力去打燈。從電(diàn)視台出來的時候,我有(yǒu)好的班底,有(yǒu)合作(zuò)慣的燈光師,他(tā)可(kě)以非常好地滿足我攝影的需要。可(kě)是後來發現,常常有(yǒu)導演總是問說:現在什麽都準備好了?打燈需要多(duō)長(cháng)時間?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我不知道燈光布置的時間,所以也答(dá)不出來。那個年代都是這樣子,問攝影師多(duō)長(cháng)時間?他(tā)總答(dá):很(hěn)快!很(hěn)快是多(duō)久?就五分(fēn)鍾吧!所有(yǒu)這些話都是緩兵之計,十分(fēn)鍾還沒好,就說再給多(duō)三分(fēn)鍾,随便應付。但是人家商(shāng)業行為(wèi)是按照部門工(gōng)作(zuò)進行的,時間控制十分(fēn)重要。後來我的攝影技(jì )術比較成熟,隻要是能(néng)控制燈光了。自己能(néng)找到好的合适的燈光師,告訴他(tā)燈從哪裏打,打什麽燈,最後差不多(duō)5分(fēn)鍾10分(fēn)鍾就可(kě)以完成了,時間控制的非常準确。所以說打燈時間的控制對成熟的攝影師是非常重要的,不能(néng)說隻顧自己的畫面,也不知道燈是怎麽打,這個制度是跟美國(guó)好萊塢DP的制度變更出來的。所以後來你看香港比較敬業的攝影師他(tā)都知道燈是怎麽打,而二線(xiàn)的攝影師要給他(tā)一個成熟的燈光師給他(tā)打燈,他(tā)控制不了打燈的時間,再來到年輕的一輩的就完全就不知道燈怎麽打了。不知道燈怎麽打燈,不知道時間的控制,就不能(néng)遵循這種商(shāng)業的流程。商(shāng)業執行你都要明白,什麽時間,燈光的器材,攝影器材,這對完成當天的工(gōng)作(zuò)很(hěn)重要。所以我從年輕的時候,在梁普智,徐克大師的戲裏慢慢變成一個能(néng)控制現場燈光的攝影師,到拍《滾滾紅塵》跟《阮玲玉》的時候控制得更好了。
當導演的眼睛

《功夫》劇照
問:您與多(duō)位導演都合作(zuò)過,像是周星馳這樣又(yòu)是導演又(yòu)是演員的,我們都說他(tā)戲内戲外截然不同,戲裏的他(tā)很(hěn)有(yǒu)喜感,是個喜劇明星,但是他(tā)戲外不怎麽愛說話。所以民(mín)間有(yǒu)許多(duō)關于他(tā)的聲音說他(tā)脾氣不好或者怎樣,但是我看您無論如何,在片場還是在片外生活當中(zhōng)對他(tā)都是非常非常支持。我就覺得這種理(lǐ)解和這種包容也能(néng)在某一個方面反映您跟導演合作(zuò)的這一個東西,因為(wèi)這對年輕人來說,攝影師和導演之間的合作(zuò)是一個永久的話題,您能(néng)不能(néng)分(fēn)享一下這樣的一個經曆。
答(dá):首先我們覺得每個電(diàn)影人的崗位問題,電(diàn)影人的崗位包括導演、攝影師、道具(jù)、美術,都是為(wèi)一個電(diàn)影而服務(wù)的。電(diàn)影是一個商(shāng)品,它不完全是個藝術品,因為(wèi)它是老闆投資的,老闆必須要有(yǒu)回報,起碼不能(néng)虧本,所以他(tā)在電(diàn)影的創作(zuò)是有(yǒu)确定的控制性和重要性。不講其它的,就講導演和攝影的關系。我說導演是講故事的人,他(tā)是把故事從他(tā)的角度,把觀衆帶進這個故事裏。攝影師是他(tā)的眼睛,他(tā)是導航,他(tā)是用(yòng)鏡頭清清楚楚解釋這些想法,所以攝影師必須要在技(jì )術上提供導演選擇,哪一種方法從導演角度去講故事可(kě)以講得更清楚,然後再變成鏡頭的運用(yòng),拍法,分(fēn)鏡頭。當然導演要有(yǒu)自己的看法,有(yǒu)些導演講得很(hěn)清楚,用(yòng)什麽運動講給攝影師,攝影師執行這個動作(zuò),比方說以前的導演告訴攝影師用(yòng)一個什麽的鏡頭,軌道從這裏移動,從半身移動到大頭特寫這樣。再來一些導演跟攝影師商(shāng)量了我想要這種氣氛,該用(yòng)什麽方法達到這個氣氛呢(ne)?對于這種導演,攝影師就要提供不同的拍攝方法,不同拍攝的角度,然後說明為(wèi)什麽這樣子,給他(tā)選擇。
還有(yǒu)一種導演是有(yǒu)想法,可(kě)是沒有(yǒu)講得很(hěn)清楚,這個時候攝影師是有(yǒu)這個責任跟他(tā)溝通,給導演需要的選擇。攝影師是幫導演完成他(tā)的故事,所以攝影師是應該有(yǒu)這種态度,溝通,滿足導演需要。不同的導演有(yǒu)不同的需要,有(yǒu)些導演是沒耐心的,那你要很(hěn)簡短很(hěn)準确地告訴他(tā);有(yǒu)些導演喜歡要很(hěn)清楚,你就要給他(tā)很(hěn)充分(fēn)地信息,講為(wèi)什麽要用(yòng)這個角度的理(lǐ)由。周星馳他(tā)戲裏戲外是同一個人,他(tā)想法比他(tā)談話快,所以他(tā)講東西時,思維已經跳到另外的地方了,到最後得出結論。這裏面很(hěn)有(yǒu)跳躍性的,要是這種導演,你必須對他(tā)的戲,電(diàn)影内容跟方向,他(tā)為(wèi)什麽要講這個故事,然後他(tā)需要什麽東西,知道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(tā)講這個鏡頭的時候你就跟這個思路去走,你就發覺很(hěn)接近,不一定完全一樣。有(yǒu)時候說中(zhōng)他(tā)要說的話、想法的時候,他(tā)就會說:“對啊,就是這樣子啦。”所以我覺得完全是溝通的問題。我覺得他(tā)的要求是合理(lǐ)的,他(tā)講不出來完全可(kě)以理(lǐ)解。其實我跟這些導演都是在片場見面,拍完電(diàn)影很(hěn)少出來喝(hē)咖啡,不是那種朋友關系。基于這種導演跟攝影師的關系,攝影師必須有(yǒu)責任去了解這個導演是需要什麽。不能(néng)說是不耐煩或是你沒有(yǒu)講好,你沒有(yǒu)告訴我做什麽。我為(wèi)什麽沒有(yǒu)對立的,因為(wèi)大家都是為(wèi)了做好這個電(diàn)影,這是唯一的目的。所以基于解決這個命題來講,所有(yǒu)都是溝通的問題。我覺得我跟他(tā)沒有(yǒu)很(hěn)難溝通的地方。可(kě)能(néng)是外界跟他(tā)的關系,我不知道,但是我不覺得他(tā)不是外界所說的那樣。

潘恒生的電(diàn)影人生
問:首先您是名(míng)電(diàn)影攝影師,也做導演,同時也是演員,然後您還是浸會大學(xué)的老師。在這麽衆多(duō)的身份當中(zhōng),您覺得電(diàn)影攝影師在您的生命中(zhōng),它到底是什麽樣的一個地位?
答(dá):我覺得我是個電(diàn)影人,電(diàn)影人就是一生都在電(diàn)影裏面工(gōng)作(zuò)。大學(xué)畢業後我是到電(diàn)視台工(gōng)作(zuò),我是攝影師,當時的我就準備投身到電(diàn)影這個行業裏。在電(diàn)視台我們還是拍菲林的,菲林的好處是你對曝光要非常準确,因為(wèi)比方說5.6光圈,要是over了,曝光過了,那後期沒有(yǒu)辦(bàn)法彌補的,這就讓我們對布光的要求有(yǒu)一個長(cháng)時間的鍛煉,這是成為(wèi)電(diàn)影人的準備功夫吧。
關于當演員,這麽多(duō)年的電(diàn)影工(gōng)作(zuò),普通觀衆隻認識我是演員。我為(wèi)什麽當了演員了呢(ne)?就是我在攝影的過程裏面,那時候香港是沒有(yǒu)打光替身的,你不能(néng)叫演員出來打光,讓演員走位給你看。通常是攝影組的人走位,因為(wèi)燈光組的人要打燈,有(yǒu)工(gōng)作(zuò)。可(kě)是這些人是有(yǒu)攝影工(gōng)作(zuò),你不能(néng)怪他(tā),他(tā)沒投入到電(diàn)影裏面,所以他(tā)光站在那邊打。但是演員出來的時候他(tā)是有(yǒu)情緒的,所以他(tā)演戲可(kě)能(néng)頭轉來轉去,結果所有(yǒu)打的燈都照不到臉上,沒有(yǒu)氣氛。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,我比較熟悉劇情,很(hěn)多(duō)時候我就走一遍給燈光師打,根據那個戲的情緒做動作(zuò)。這個過程中(zhōng),導演就會在監視器前看你看你怎麽演戲,有(yǒu)的說這個戲不錯,就找你演。大部分(fēn)街(jiē)道上的普通觀衆就覺得我是個演員,從來不叫我是個攝影師,其實是工(gōng)作(zuò)上的需要變成一個演員。
而攝影這一部分(fēn)的工(gōng)作(zuò)直到2010年,工(gōng)作(zuò)時間比較空閑一點,跟卓伯棠,他(tā)是博士,搞正規電(diàn)影學(xué)習設計總監,跟他(tā)碰過我幾次。然後就邀請我到他(tā)們學(xué)校,說是時候要回饋給學(xué)校。當攝影師以後空閑的時間一直定不下來,因為(wèi)教書要定下時間。2010年我比較空閑一些,又(yòu)經不起他(tā)這麽多(duō)次找我,就開始跑到浸會裏面開始教書,傳承一下。還是因為(wèi)這麽多(duō)年在電(diàn)影圈的生涯,也有(yǒu)點經驗,跟小(xiǎo)朋友講一下。主要我覺得講的不是技(jì )巧性的東西,尤其是現在數碼變更得很(hěn)快。我能(néng)給學(xué)生的是方向性的東西,因為(wèi)畢竟我在片場、在電(diàn)影圈這麽多(duō)年的生活,知道怎麽可(kě)以生存,應該注意什麽,我希望把這些東西給年輕人,就是有(yǒu)勵志(zhì)在這個電(diàn)影行業發展的人一點經驗的啓示,讓他(tā)們不要多(duō)走冤枉路。我覺得我是個電(diàn)影人,電(diàn)影人其實是離不開的電(diàn)影,不管是教書,還是做電(diàn)影攝影師,都是在一個世界裏面。
潘恒生的電(diàn)影思維

《小(xiǎo)夜刀(dāo)》劇照
問:我之前看過一篇文(wén)章說我們這一代所謂的青年影迷都是受電(diàn)視的影響比較深,我們從小(xiǎo)都是看電(diàn)視或者是吃着爆米花(huā)看着美國(guó)大片出來的。所以我們的電(diàn)影思維比較差。那作(zuò)為(wèi)一個電(diàn)影攝影師來說,究竟什麽是個大熒幕的思維?
答(dá):我覺得最簡單的講法,因為(wèi)我出身也是電(diàn)視台的攝影師,當年我也是拍了很(hěn)多(duō)電(diàn)視劇的東西,用(yòng)的也是菲林,它非常接近電(diàn)影的表現手法。到我出來拍電(diàn)影的時候,我有(yǒu)一部戲叫《生死線(xiàn)》,這個戲是梁普智導演的,他(tā)原來是一個拍廣告的。你知道廣告是對攝影非常講究,因為(wèi)廣告在香港來講隻有(yǒu)30秒(miǎo),所以一個鏡頭裏面要講很(hěn)多(duō)東西,非常講究角度,拍什麽東西,光線(xiàn),大小(xiǎo)。他(tā)一直都是這種導演,所以他(tā)對這個電(diàn)影攝影要求非常高,特别能(néng)用(yòng)鏡頭講故事。他(tā)很(hěn)多(duō)次都問我,怎麽設計那個鏡頭,問我這場戲今天怎麽拍,那我就想搖一個吧,從A搖到B,軌道推進去。那時候劇本不是那麽全的,拍一場我就來看哪一場的劇本,所以這個戲當然是導演最清楚,然後他(tā)就根據我的建議,從戲裏面想,就說有(yǒu)點不對,好像不是A拍到B啊,是從B拉出來,看到AB兩個人才對。那好吧,導演都這麽說了。後來他(tā)又(yòu)問了,這個鏡頭怎麽設計?我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當然是要給他(tā)答(dá)案選擇,我就說兩個人推近一個人。他(tā)就想,是應該一個人拉出來,他(tā)老是這樣改我的鏡頭我生氣了,這又(yòu)不是我的工(gōng)作(zuò)。你要我提供想法你不能(néng)批評我,年輕人嘛,就這樣。
後來有(yǒu)一個鏡頭,我們在《生死線(xiàn)》裏面有(yǒu)一個湖(hú),中(zhōng)間有(yǒu)個樹,戲裏面有(yǒu)個壞人挂在樹上面。他(tā)就問我,這個鏡頭應該怎麽拍?我就說開始從兩個身上,然後一直拉到全景看到整個湖(hú)中(zhōng)間有(yǒu)棵樹上面人在上面,這樣的鏡頭蠻厲害的。他(tā)就想,這個不對啊,這個鏡頭不是電(diàn)影鏡頭,什麽是電(diàn)影鏡頭,講故事嘛,要讓觀衆非常感動,因為(wèi)觀衆是付錢看電(diàn)影的,你老是想這種電(diàn)視的鏡頭。電(diàn)視上面觀衆沒要求的,他(tā)不用(yòng)付款,不喜歡他(tā)不會說話的。可(kě)是到戲院裏面他(tā)付錢,看到這種電(diàn)視的鏡頭他(tā)不如回家看電(diàn)視。那個時候我生氣是因為(wèi)你叫我講就講,你批評我幹嘛。可(kě)是這話就說出電(diàn)視和電(diàn)影鏡頭的分(fēn)别,戲院裏看觀衆要有(yǒu)滿足感,他(tā)付錢是有(yǒu)要求的。電(diàn)影人講鏡頭不能(néng)說随随便便把故事講出來就夠了,必須要有(yǒu)不同的角度,不同的驚喜,讓觀衆覺得滿足,這才是電(diàn)影的鏡頭。所以這話在我的電(diàn)影生涯裏面影響非常大,就是每當想随便拍個鏡頭,這個句話就會提醒我,觀衆是付錢的來看這個鏡頭的,不能(néng)馬虎,必須用(yòng)心設計,讓觀衆得到滿足,這才是電(diàn)影人,這個鏡頭才是講故事,電(diàn)影不管是鏡頭、内容、演戲、後台都要講究。從這個事情我學(xué)到了很(hěn)多(duō)。
從《似水流年》到《阮玲玉》

《似水流年》劇照 (斯琴高娃 / 顧美華)(DP 潘恒生 HKSC)
問:潘老師,您是香港電(diàn)影新(xīn)浪潮的領頭人,當年和嚴浩先生合作(zuò)的《似水流年》讓我們都印象十分(fēn)深刻,裏面那個舒緩的鏡頭真的特别特别柔美。到包括後來金像獎最佳攝影師《阮玲玉》,這部電(diàn)影有(yǒu)很(hěn)多(duō)影迷,有(yǒu)一年電(diàn)影資料館還放膠片版,就是菲林版,觀看的人非常的多(duō)。那應該是您年輕的時候一個創作(zuò)初期,您能(néng)不能(néng)跟大家分(fēn)享一下對這種新(xīn)事物(wù)的接受和您當時創作(zuò)的心境,對電(diàn)影的觀念。
答(dá):《似水流年》其實算是我第二部電(diàn)影,第一部電(diàn)影是《我為(wèi)你狂》,金炳興當導演,他(tā)是一個很(hěn)出名(míng)的編劇當導演,可(kě)惜這部戲我沒能(néng)夠完成。當時我還在電(diàn)視台工(gōng)作(zuò),然後被請去就拍《似水流年》,《似水流年》算是第一部從香港到大陸來拍的電(diàn)影。那時候82、83年,我們年輕,經驗也不多(duō),拍攝的時候廣州我們也去過,北京上海我們也去過,一直到汕頭那個地方,那裏很(hěn)有(yǒu)農村的感覺。
我們到那個農村導演就說這是從明朝開始保留的原貌,沒有(yǒu)改變過,特别幸運。當時我們因為(wèi)年輕,看那個地方唯一的感覺就是很(hěn)有(yǒu)生命力,牲畜都跟路上的泥土混在一起。我們香港比較講究潔癖,可(kě)是沒辦(bàn)法,整天鞋子上都是泥和糞便,這種生活給住在樓層的人有(yǒu)非常驚喜和震撼的感覺。《似水流年》的時候我們剛從電(diàn)視台出來,突然變成拍電(diàn)影。我們就重新(xīn)要學(xué),重新(xīn)要歸納我們懂的東西到新(xīn)的平台上去。雖然那個電(diàn)影是個文(wén)藝片,比較容易操控,但是在曝光方面,對我來講,是要重新(xīn)看整個畫面的曝光,是不是都在菲林的寬銀幕裏面,怎麽表現出來。我覺得這是我離開香港一個本土的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的适應能(néng)力發揮出來的一種應變能(néng)力。

《阮玲玉》劇照
到拍《阮玲玉》比較成熟了。《阮玲玉》也是到大陸來拍,90年的時候。大陸經濟開發差不多(duō)可(kě)以了。我們那時候到上海,那裏是個繁華的都市,有(yǒu)新(xīn)的東西,也有(yǒu)蠻舊的,像上個世紀的弄堂,是1920年遺留下來的一種文(wén)化沉澱。在拍《阮玲玉》很(hěn)多(duō)時候用(yòng)的是很(hěn)舊的景,現在可(kě)能(néng)已經拆掉了。那時候我們看那個景都是1920年、1930年的,特别生活,特别文(wén)化的一種感覺。《阮玲玉》特别要提的是美術指導配合非常好。老實說攝影其實是拍一個東西,所以沒有(yǒu)美景,沒有(yǒu)漂亮的演員,沒有(yǒu)漂亮的服裝(zhuāng),你那個攝影不可(kě)能(néng)特别漂亮的,超越别人的。那個時候我是覺得,第一,很(hěn)多(duō)很(hěn)懷舊很(hěn)有(yǒu)風味的景我們可(kě)以拍,另外就是美術要做好。舉例就是阮玲玉住的那個地方,其實我們就在她住的不多(duō)遠(yuǎn)的地方拍,那個床原來擺着的。美術指導找出那個年代的衣服,叫美術學(xué)院的學(xué)生照着衣服上的圖案畫出來。影片裏那個商(shāng)場都是畫出來的,他(tā)們花(huā)了一個月的時間畫到牆上面。本來我們跟這個地方的房東講,這個樓借三個月給我們拍,然後屋主說你們是要還原白牆的。最後看到我們這麽漂亮的房間他(tā)就不用(yòng)還原了,太漂亮了,就保留這個。

《阮玲玉》劇照
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拍《阮玲玉》的時候我們用(yòng)光突出人物(wù),景跟人物(wù)的光的反差對比比較大。我們在拍的時候就盡量把反差控制,光打人就打人,就不會掉到牆上面,不會擋住這樣。然後加上美術,加上這個服裝(zhuāng)和發型,這個環境,這個人物(wù)定位就特别準。我覺得這整體(tǐ)的配合就變成這個電(diàn)影。《似水流年》和《阮玲玉》兩部電(diàn)影,《阮玲玉》運動比較多(duō),《似水流年》運動比較少。兩個戲的拍攝的環境、拍攝的條件都給我非常充分(fēn)的攝影發揮機會。
你覺得我有(yǒu)攝影風格?

《大話西遊》劇照
問:您之前拍文(wén)藝片比較多(duō),到後來您又(yòu)拍出來像《縱橫四海》、《大話西遊》、《功夫》、《長(cháng)江七号》,這一系列在商(shāng)業史上既叫好又(yòu)叫座的片子。這就感覺跟您的多(duō)重身份一樣,我們知道您既在藝術片運境上面有(yǒu)一定的見解,又(yòu)在商(shāng)業片中(zhōng)又(yòu)遊刃有(yǒu)餘,所以您是怎麽看待自己的攝影風格的呢(ne)?
答(dá):因為(wèi)我當攝影師這麽多(duō)年,一年接兩部戲,我不喜歡有(yǒu)戲重疊的。有(yǒu)些人是一部戲拍得差不多(duō),他(tā)就又(yòu)接另一部戲,然後叫人家頂最後幾天。我不習慣,我習慣一部戲完結了,再接另外一部戲。我是比較少産(chǎn)的攝影師。我從來不看自己是什麽風格的。我記得很(hěn)久以前有(yǒu)個雜志(zhì)訪問就問這個問題:潘先生您攝影的風格是什麽?我說:你覺得我有(yǒu)攝影風格?那你告訴我,我的風格是什麽?然後他(tā)舉個例子,有(yǒu)一部戲他(tā)問那個導演:這個戲是不是第一場戲是潘恒生攝影的,之後就沒有(yǒu)他(tā)了,确實是這樣!因為(wèi)我沒有(yǒu)接這個戲,他(tā)要補戲的時候找我,去補了一場。我問他(tā)怎麽知道,他(tā)說是因為(wèi)我那個風格是很(hěn)多(duō)軌道走動的。我為(wèi)什麽喜歡用(yòng)軌道,因為(wèi)我覺得電(diàn)影是兩維的東西,觀衆投入到兩維的世界裏面。電(diàn)影好玩的地方是把觀衆帶進那個立體(tǐ)的世界裏面,好像旅遊一樣,你進來看看,左看看右看看前面看看後面,這樣從兩維變成三維空間的感覺要用(yòng)軌道帶出來,改變那個視覺視點,變成整個世界是立體(tǐ)的,這樣講出來的故事才能(néng)讓觀衆感同身受。這是我常用(yòng)軌道的原因。其實拍每一部電(diàn)影都是我看了劇本,跟導演溝通以後就投入到故事裏面。每一個電(diàn)影故事它有(yǒu)不同需要,我就盡我所能(néng)去滿足。我沒有(yǒu)預定我要拍文(wén)藝片,然後準備拍動作(zuò)片,然後準備拍商(shāng)業片。我是比較随意的那種,是機遇讓我變成這個樣。

《佛萊迪大戰傑森》劇照
電(diàn)影的人員分(fēn)工(gōng)是很(hěn)清楚,因為(wèi)這是商(shāng)業的行為(wèi)。攝影就隻顧攝影的東西,燈光就顧燈光的部分(fēn),有(yǒu)的攝影師比較被動,他(tā)不能(néng)靠自己能(néng)力去打燈。從電(diàn)視台出來的時候,我有(yǒu)好的班底,有(yǒu)合作(zuò)慣的燈光師,他(tā)可(kě)以非常好地滿足我攝影的需要。可(kě)是後來發現,常常有(yǒu)導演總是問說:現在什麽都準備好了?打燈需要多(duō)長(cháng)時間?作(zuò)為(wèi)攝影師我不知道燈光布置的時間,所以也答(dá)不出來。那個年代都是這樣子,問攝影師多(duō)長(cháng)時間?他(tā)總答(dá):很(hěn)快!很(hěn)快是多(duō)久?就五分(fēn)鍾吧!所有(yǒu)這些話都是緩兵之計,十分(fēn)鍾還沒好,就說再給多(duō)三分(fēn)鍾,随便應付。但是人家商(shāng)業行為(wèi)是按照部門工(gōng)作(zuò)進行的,時間控制十分(fēn)重要。後來我的攝影技(jì )術比較成熟,隻要是能(néng)控制燈光了。自己能(néng)找到好的合适的燈光師,告訴他(tā)燈從哪裏打,打什麽燈,最後差不多(duō)5分(fēn)鍾10分(fēn)鍾就可(kě)以完成了,時間控制的非常準确。所以說打燈時間的控制對成熟的攝影師是非常重要的,不能(néng)說隻顧自己的畫面,也不知道燈是怎麽打,這個制度是跟美國(guó)好萊塢DP的制度變更出來的。所以後來你看香港比較敬業的攝影師他(tā)都知道燈是怎麽打,而二線(xiàn)的攝影師要給他(tā)一個成熟的燈光師給他(tā)打燈,他(tā)控制不了打燈的時間,再來到年輕的一輩的就完全就不知道燈怎麽打了。不知道燈怎麽打燈,不知道時間的控制,就不能(néng)遵循這種商(shāng)業的流程。商(shāng)業執行你都要明白,什麽時間,燈光的器材,攝影器材,這對完成當天的工(gōng)作(zuò)很(hěn)重要。所以我從年輕的時候,在梁普智,徐克大師的戲裏慢慢變成一個能(néng)控制現場燈光的攝影師,到拍《滾滾紅塵》跟《阮玲玉》的時候控制得更好了。
當導演的眼睛

《功夫》劇照
問:您與多(duō)位導演都合作(zuò)過,像是周星馳這樣又(yòu)是導演又(yòu)是演員的,我們都說他(tā)戲内戲外截然不同,戲裏的他(tā)很(hěn)有(yǒu)喜感,是個喜劇明星,但是他(tā)戲外不怎麽愛說話。所以民(mín)間有(yǒu)許多(duō)關于他(tā)的聲音說他(tā)脾氣不好或者怎樣,但是我看您無論如何,在片場還是在片外生活當中(zhōng)對他(tā)都是非常非常支持。我就覺得這種理(lǐ)解和這種包容也能(néng)在某一個方面反映您跟導演合作(zuò)的這一個東西,因為(wèi)這對年輕人來說,攝影師和導演之間的合作(zuò)是一個永久的話題,您能(néng)不能(néng)分(fēn)享一下這樣的一個經曆。
答(dá):首先我們覺得每個電(diàn)影人的崗位問題,電(diàn)影人的崗位包括導演、攝影師、道具(jù)、美術,都是為(wèi)一個電(diàn)影而服務(wù)的。電(diàn)影是一個商(shāng)品,它不完全是個藝術品,因為(wèi)它是老闆投資的,老闆必須要有(yǒu)回報,起碼不能(néng)虧本,所以他(tā)在電(diàn)影的創作(zuò)是有(yǒu)确定的控制性和重要性。不講其它的,就講導演和攝影的關系。我說導演是講故事的人,他(tā)是把故事從他(tā)的角度,把觀衆帶進這個故事裏。攝影師是他(tā)的眼睛,他(tā)是導航,他(tā)是用(yòng)鏡頭清清楚楚解釋這些想法,所以攝影師必須要在技(jì )術上提供導演選擇,哪一種方法從導演角度去講故事可(kě)以講得更清楚,然後再變成鏡頭的運用(yòng),拍法,分(fēn)鏡頭。當然導演要有(yǒu)自己的看法,有(yǒu)些導演講得很(hěn)清楚,用(yòng)什麽運動講給攝影師,攝影師執行這個動作(zuò),比方說以前的導演告訴攝影師用(yòng)一個什麽的鏡頭,軌道從這裏移動,從半身移動到大頭特寫這樣。再來一些導演跟攝影師商(shāng)量了我想要這種氣氛,該用(yòng)什麽方法達到這個氣氛呢(ne)?對于這種導演,攝影師就要提供不同的拍攝方法,不同拍攝的角度,然後說明為(wèi)什麽這樣子,給他(tā)選擇。
還有(yǒu)一種導演是有(yǒu)想法,可(kě)是沒有(yǒu)講得很(hěn)清楚,這個時候攝影師是有(yǒu)這個責任跟他(tā)溝通,給導演需要的選擇。攝影師是幫導演完成他(tā)的故事,所以攝影師是應該有(yǒu)這種态度,溝通,滿足導演需要。不同的導演有(yǒu)不同的需要,有(yǒu)些導演是沒耐心的,那你要很(hěn)簡短很(hěn)準确地告訴他(tā);有(yǒu)些導演喜歡要很(hěn)清楚,你就要給他(tā)很(hěn)充分(fēn)地信息,講為(wèi)什麽要用(yòng)這個角度的理(lǐ)由。周星馳他(tā)戲裏戲外是同一個人,他(tā)想法比他(tā)談話快,所以他(tā)講東西時,思維已經跳到另外的地方了,到最後得出結論。這裏面很(hěn)有(yǒu)跳躍性的,要是這種導演,你必須對他(tā)的戲,電(diàn)影内容跟方向,他(tā)為(wèi)什麽要講這個故事,然後他(tā)需要什麽東西,知道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他(tā)講這個鏡頭的時候你就跟這個思路去走,你就發覺很(hěn)接近,不一定完全一樣。有(yǒu)時候說中(zhōng)他(tā)要說的話、想法的時候,他(tā)就會說:“對啊,就是這樣子啦。”所以我覺得完全是溝通的問題。我覺得他(tā)的要求是合理(lǐ)的,他(tā)講不出來完全可(kě)以理(lǐ)解。其實我跟這些導演都是在片場見面,拍完電(diàn)影很(hěn)少出來喝(hē)咖啡,不是那種朋友關系。基于這種導演跟攝影師的關系,攝影師必須有(yǒu)責任去了解這個導演是需要什麽。不能(néng)說是不耐煩或是你沒有(yǒu)講好,你沒有(yǒu)告訴我做什麽。我為(wèi)什麽沒有(yǒu)對立的,因為(wèi)大家都是為(wèi)了做好這個電(diàn)影,這是唯一的目的。所以基于解決這個命題來講,所有(yǒu)都是溝通的問題。我覺得我跟他(tā)沒有(yǒu)很(hěn)難溝通的地方。可(kě)能(néng)是外界跟他(tā)的關系,我不知道,但是我不覺得他(tā)不是外界所說的那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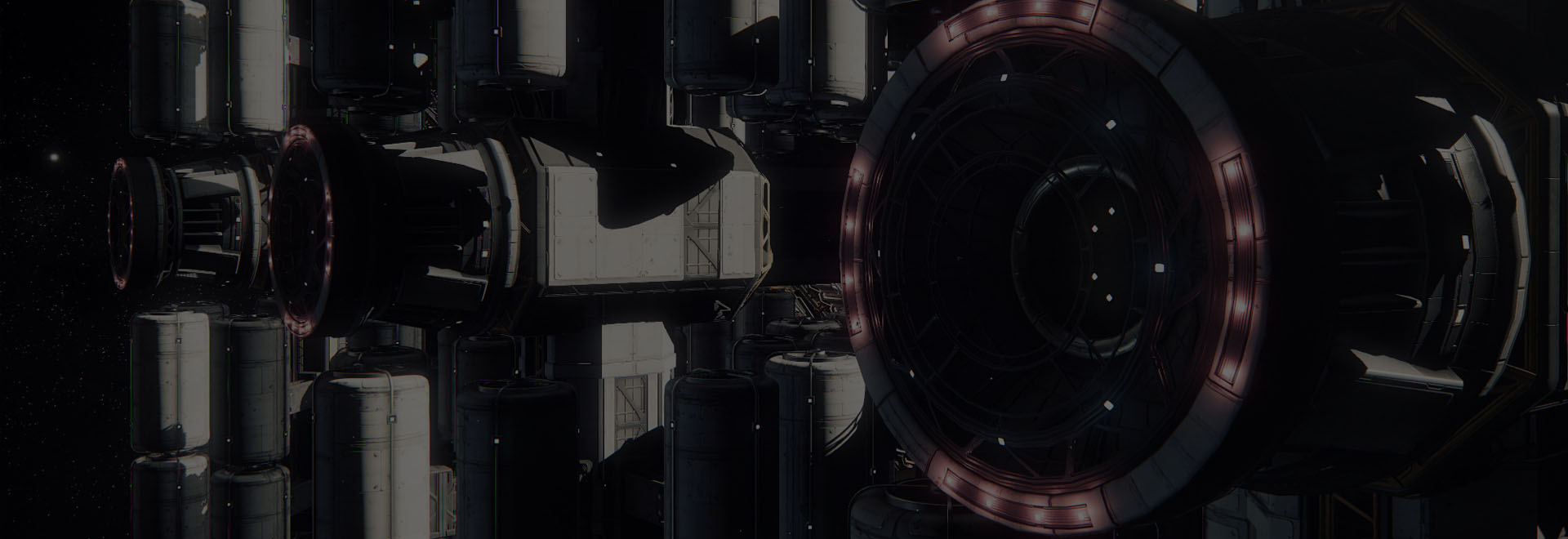


 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
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