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斯皮爾伯格可(kě)以說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導演之一,其執導的電(diàn)影《大白鲨》、《E.T.外星人》以及《侏羅紀公(gōng)園》分(fēn)别在當時打破了票房記錄,成為(wèi)做賣座的電(diàn)影。而這位大導演并不是純正科(kē)班出身的電(diàn)影創作(zuò)者,在加州大學(xué)就讀不久後就休學(xué)開始拍片,一直到 2000 年後才真正拿(ná)到大學(xué)文(wén)憑。适逢畢業季,斯皮爾伯格日前到了哈佛大學(xué)為(wèi)應屆畢業生緻詞,他(tā)以電(diàn)影創作(zuò)的過程來比拟生活,鼓勵畢業生要在這個布滿怪物(wù)的世界裏,找出自己最獨特的定位。
(視頻沒有(yǒu)字幕,介意可(kě)以直接反下面的文(wén)章)
“我的父親在我 12 歲的時候給了我一台攝影機,而攝影機則成為(wèi)了我讓這個世界合理(lǐ)化的工(gōng)具(jù)。不過這個世界滿滿的都是怪物(wù)。…你們接下來選擇要做的事情,就是我們在制作(zuò)電(diàn)影時所做的“定義角色”,不過在電(diàn)影裏面你有(yǒu)兩個小(xiǎo)時來定義一個角色,但在現實生活裏,你每天都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,生命就是一連串的角色定義時刻。
當斯皮爾伯格25 歲時,他(tā)開始了解傾聽自己内心聲音的重要性,而他(tā)也希望畢業生透過自己的直覺,找到盡管冒險,但還是在自己能(néng)夠挑戰範圍内的最高目标。
“我開始注意我的直覺告訴我的事情,我必須要清楚地告訴你們,直覺和你們的意識是截然不同的,你的意識可(kě)能(néng)會對着你大喊這些是你該做的,但你的直覺可(kě)能(néng)會在你耳邊輕聲說這是你可(kě)以做的。你必須聆聽這個聲音,這是最能(néng)定義你角色的聲音。"
在緻詞的過程中(zhōng),斯皮爾伯格以自己的生涯發展舉例,他(tā)表示在 1980 年代,他(tā)的電(diàn)影作(zuò)品是最逃避現實的一種,他(tā)就像是活在膠片片的泡泡裏面,一直到拍攝《紫色》才改變了他(tā)的想法。
“在拍攝這部電(diàn)影時,我才了解到電(diàn)影也可(kě)以是一種使命。不要懼怕痛苦的事情,要衡量它,然後挑戰它。”
不過就在斯皮爾伯格贊揚教育必要性的同時,他(tā)也談到當時為(wèi)什麽決然離開學(xué)校,開始在電(diàn)影全工(gōng)作(zuò),也開玩笑表示因為(wèi)拍攝《侏羅紀公(gōng)園》,讓他(tā)拿(ná)到了考古學(xué)的學(xué)分(fēn)。
“在大二的時候環球影業給了我一份我夢想中(zhōng)的工(gōng)作(zuò),所以我決定放棄讀書,我告訴我的父母,如果拍電(diàn)影這條路發展的不好,我就會重新(xīn)去上學(xué),結果它發展的很(hěn)好。”
在整段緻詞的最後,斯皮爾伯格鼓勵所有(yǒu)的畢業生,要好好地研讀過去,才能(néng)夠在現在活的充實。
“我并不是要拿(ná)曆史來當做說教的工(gōng)具(jù),而是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充滿了最棒的故事。我們的國(guó)家現在充滿着移民(mín),至少現在是這樣,對我來說,這就代表了我們有(yǒu)更多(duō)的故事要訴說。”
關于斯皮爾伯格的拍片經曆我們發過一次很(hěn)長(cháng)的訪談,他(tā)從斯皮爾伯格聊起,詳細講說了他(tā)拍片的過程、想法,這個對于認識電(diàn)影和這個人真的很(hěn)有(yǒu)幫助。
有(yǒu)人說你的導演生涯是在為(wèi)環球拍片的時候開始的,這是對的嗎?
老斯:也不是,是在環球雇我之前就開始了。我在亞利桑那念高中(zhōng)的時候,一次我去拜訪我的堂兄們,我在那裏玩了一天,當時有(yǒu)種叫“灰線(xiàn)旅遊”的東西,正午的時候每個人可(kě)以去洗澡。所以那天正午我躲在浴室裏,等到所有(yǒu)人都走了。一個小(xiǎo)時之後我才出來,除了我就沒有(yǒu)什麽人了,我自由了。我當時就跑到環球公(gōng)司裏去了。我遇到了一個膠片管理(lǐ)員,叫Chuck Silvers,他(tā)覺得我挺有(yǒu)種的,就讓我在那裏自由玩了3天,所以我就那裏拍片了。後來我就在那裏呆了兩個半月,一個星期呆5天,直到要開學(xué)了,我才回家去。
那個時候你就想當一個導演的了嗎?
老斯:還沒有(yǒu)。那時候我從沒想過我會做些什麽和電(diàn)影有(yǒu)關的大事。當時我隻是被電(diàn)影裏的東西迷住了,像火車(chē)失事那樣的場面我會看個好幾遍。我懂得了可(kě)以通過另一種媒介來認知生活,并讓生活變得更好。我當時拍的是那種8mm 的小(xiǎo)破電(diàn)影,我也意識到拍這樣的電(diàn)影讓我感覺很(hěn)好。我還覺得也許我可(kě)以把更多(duō)人帶進這種神奇的東西之中(zhōng),讓他(tā)們在裏面好好享受。
後來,因為(wèi)你拍的一部短片,得以回到環球去拍電(diàn)視劇。這個階段你的技(jì )巧是如何突飛猛進的呢(ne)?
老斯:Sid Sheinberg給我了份七年的合同,讓我去拍電(diàn)視劇。我感覺很(hěn)好,像回家了一樣。拍電(diàn)視可(kě)以說是在畢業之後拍電(diàn)影之前的過渡項目,那是一個學(xué)習的過程。我從未職業地拍過什麽東西,劇組裏的人也跟我差不多(duō)歲數,那時我正在拍我的第一個的電(diàn)視節目叫《Night Gallery》,Joan Crawford是主演。這時候劇組人員有(yǒu)超過75個吧,平均年齡50歲左右。所以,第一天拍片的時候,我帶着我臉上的青春痘和長(cháng)發露面,脖子還煞有(yǒu)其事地挂着一個取景器,我覺得那些大人們一定看了我一眼然後心裏想,這小(xiǎo)屁孩最好趕緊露兩手,不然就趕緊滾蛋。他(tā)們挺為(wèi)難我的,一直慢吞吞地做事,但是這樣他(tā)們不會被炒但我有(yǒu)可(kě)能(néng)會被炒,這種情況像一次洗禮一樣。
我意識到,有(yǒu)一天我一定要獲得最後的剪輯權。因為(wèi)電(diàn)視導演是沒有(yǒu)剪輯的權力。後期制作(zuò)開始,剪輯就接管了影片,然後制片也會進來,這樣一來,你拍過的片就會被再剪一次,有(yǒu)時會剪得過頭,有(yǒu)時他(tā)們也不明白你拍的畫面的意思。我就意識到,我的目标就是某一天我要得到我電(diàn)影的所有(yǒu)控制權。
兩年後你拍了第一部電(diàn)影,《決鬥》,你當時是怎麽得到這個拍片的機會的呢(ne)?
老斯:我遊說了很(hěn)久,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。當時我剛導完《Colombo》的第一集,反響很(hěn)不錯。我把這集的大概剪輯給了George Eckstein看,他(tā)是《決鬥》的制片人。他(tā)很(hěn)喜歡。于是就幫我去跟别人說了,我覺得他(tā)應該去找了Barry Diller,他(tā)當時是ABC的頭兒。Barry同意了,于是我就得到了這個機會。
你做了哪些準備呢(ne)?
老斯:當時我已經拍過七八集電(diàn)視劇,這些劇是不同的類型。所以當時我認為(wèi)拍電(diàn)影應該會好受些吧。因為(wèi)我有(yǒu)11天的時間,來拍一個74分(fēn)鍾的電(diàn)視電(diàn)影。我們到了沙漠裏去。然後我沒有(yǒu)畫分(fēn)鏡表,但是有(yǒu)人幫我畫好了故事的脈絡,我在上面畫了好多(duō)倒V,意思這裏那裏是放攝影機的,因為(wèi)有(yǒu)場要拍汽車(chē)追逐戲,在高速公(gōng)路上,有(yǒu)五個攝影機五個鏡頭,我們就能(néng)拍到很(hěn)多(duō)的鏡頭。然後把車(chē)掉頭,換一個鏡頭,再重新(xīn)拍一遍,這樣一來,就有(yǒu)了兩個方向的素材了。
這個電(diàn)影我得到很(hěn)多(duō)誇獎,誇我說我把《決鬥》拍得很(hěn)有(yǒu)懸念,很(hěn)希區(qū)柯克,但是其實Richard Matheson的劇本就已經很(hěn)希區(qū)柯克很(hěn)引人入勝了。我覺得這應該我第一次這麽覺得,“嘿,我要是有(yǒu)個好劇本的話,那我一定能(néng)拍出超棒的電(diàn)影。”對,應該是這個時候我也開始覺得,好導演要有(yǒu)好劇本的支持。
你的第一部劇情片《橫沖直撞大逃亡》的主題是“孤獨的小(xiǎo)孩子“,這個主題似曾相識。你當時已經有(yǒu)注意到自己的這個傾向了嘛?
老斯:不是太清楚我在拍《橫》的時候對此有(yǒu)什麽想法,我是根據報紙上的某篇文(wén)章寫出的這個故事。報紙上是說有(yǒu)對夫妻要把他(tā)們的baby從孤兒院接回來怎麽怎麽地,後來就被我發展成了那個瘋狂的故事了。懷爾德(dé)的《倒扣的王牌》一直是我的最愛之一。這片子真的影響我很(hěn)多(duō),比如裏面悲劇形勢下那種狂歡的氛圍和對資本化和剝削的表現。
《大白鲨》在你的生涯是個裏程碑啊,對于拍攝的那段時間你有(yǒu)什麽好的回憶嗎?
老斯:《大白鲨》的成功得歸功于很(hěn)多(duō)東西,其中(zhōng)一個是我有(yǒu)了最終剪輯權。我有(yǒu)了創作(zuò)的自由,但是拍《大白鲨》對我來說卻是一個可(kě)怕的經曆。原因之一是,劇本一直沒有(yǒu)完成的,我們隻能(néng)邊拍邊寫。
每個人都叫我不要在水裏拍,Sid Sheinberg甚至說,“為(wèi)什麽不建個水箱呢(ne)?我們會給你錢的。”但是我說,不用(yòng)了,我想到海裏去拍,去認真試一試,我要讓觀衆覺得這是真的,鲨魚真的在海裏面。我不想讓這部片變得像《老人與海》那樣的電(diàn)影,背景一看就是畫的。
那你是怎麽想到要拍《侏羅紀公(gōng)園》的?
老斯:我想應該是在看邁克·克萊頓的小(xiǎo)說時,我當時還想到了《決鬥》。真的,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與恐龍有(yǒu)關的電(diàn)影。
《侏》是部CG電(diàn)影。你當時有(yǒu)意識到CG領域裏的巨變嗎?
老斯:CG第一次用(yòng)到商(shāng)業電(diàn)影裏,是在我制片、Barry Levinson導演的《少年福爾摩斯》裏。ILM(工(gōng)業光魔)制造出了彩色窗上的騎士突然變成真的,然後跳出窗子的效果。這甚至是第一次數碼特效在商(shāng)業上的運用(yòng)。當然,第二個用(yòng)的比較好就是卡梅隆的《深淵》,裏面用(yòng)了很(hěn)多(duō)極緻的數字特效。但是,用(yòng)數字恐龍來做電(diàn)影主角這個事情還沒人做過。所以,可(kě)以這麽說,《侏羅紀公(gōng)園》是第一步把成敗賭在數字特效好壞的電(diàn)影。
當年你和盧卡斯在夏威夷海灘聊天的時候,是怎麽考慮這個故事的呢(ne)?
老斯:我1977年到夏威夷見到盧卡斯的時候,差不多(duō)是《星球大戰》正好上映的時候。當時他(tā)的手機響了,得知票房很(hěn)好,于是他(tā)很(hěn)開心。也是在這樣的喜悅之中(zhōng),我們馬上開始想想未來該做些什麽。他(tā)問我接下來準備幹嗎,我說我也不太确定,但是有(yǒu)點想再試試說服Cubby Broccoli讓我導部007的電(diàn)影。哦,順便說一下,Cubby Broccoli已經拒絕過我兩次了。這時候盧卡斯說,我有(yǒu)個更好的東西,比007還好,叫做《奪寶奇兵》。
《大白鲨》和《第三類接觸》都是商(shāng)業上很(hěn)成功的電(diàn)影,之後你拍了《1941》,在這之間是發生了什麽事嗎?
老斯:我是想要拍一部真正有(yǒu)趣的電(diàn)影。我之前從沒有(yǒu)拍過喜劇片,不過之後我也再沒拍過喜劇片了。但我想試一試,結果票房并不好。但是我想說,我在拍這部片的時候,我一直覺得自己一定會成功的。我覺得裏面的每個笑點大家都會笑,而且還會報以掌聲。工(gōng)作(zuò)人員和演員都會拿(ná)奧斯卡獎,這片的拍攝周期是最長(cháng)的,我甚至還拖延了點時間,比拍《大白鲨》拖得還久,但是很(hěn)快我就醒悟了。每當我回憶這段曆史的時候,我覺得不是我做錯了,不是我的問題,隻是我當時太想把所有(yǒu)事情都做對,我不能(néng)把工(gōng)作(zuò)分(fēn)給别人做。我在拍《1941》的時候學(xué)到了我生涯中(zhōng)最重要的教訓。于是在拍《奪寶奇兵》的時候,我變得謙虛多(duō)了,每個鏡頭我都有(yǒu)畫分(fēn)鏡表,于是我比計劃快了14天完成。
再後來,《太陽帝國(guó)》和《世界之戰》又(yòu)是完全不同的片子了。是什麽機緣巧合讓你拍這兩部片的呢(ne)?
老斯:我是大衛·裏恩的朋友,有(yǒu)一次他(tā)打電(diàn)話給我說:“這裏有(yǒu)本我挺想拍成電(diàn)影的書,是J. G. Ballard的《太陽帝國(guó)》。我知道版權好像在華納兄弟(dì)那邊。你可(kě)以幫我搞來嗎?”我去做了。我打電(diàn)話給了華納的老闆,J. G. Ballard。他(tā)說有(yǒu)個導演已經要走這個故事了,而且Tom Stoppard已經在寫劇本了。所以我打回去給大衛·裏恩,告訴他(tā)這片已經有(yǒu)人要了。然後大概六七個月後,Semel打電(diàn)話給我說事情有(yǒu)變。于是我打給裏恩,當時他(tā)卻不想拍這片了。他(tā)說:“你應該去拍。我覺得你可(kě)以做好的。”
《辛德(dé)勒的名(míng)單》似乎是你拍得最艱難的一部?從技(jì )術層面來說也是如此。當時把這片給你拍的時候你有(yǒu)拒絕嗎?
老斯:是Sid Sheinberg找到的這故事。他(tā)對我說:“我覺得你應該把這個故事拍出來。”于是他(tā)就把這個故事買下來了。但是在那時候,我覺得我還駕馭不了猶太人大屠殺這種題材,而且我那時候還有(yǒu)很(hěn)多(duō)片可(kě)以拍,有(yǒu)些已經做了準備了。拍了《奪寶奇兵2》再拍《辛德(dé)勒》跨越太大,太難了。我覺得自己還不夠成熟,不管是自己的拍電(diàn)影的水平,還是對于表現大屠殺的情緒上的準備。我就一直想把這個片推給别人拍,但是他(tā)們都又(yòu)推回給我。
這部電(diàn)影人們談論的最多(duō)的畫面是辛德(dé)勒往下看看到穿紅衣的小(xiǎo)女孩的那個鏡頭。這個場景是虛構的嗎?
老斯:不是,是确有(yǒu)其事。某天早晨,辛德(dé)勒和他(tā)的女朋友在克拉科(kē)夫猶太區(qū)親眼看到的。他(tā)當時正在騎馬,然後聽到一片嘈雜,各種各樣的交通工(gōng)具(jù)在猶太區(qū)穿行。我們在和辛德(dé)勒同樣的視角拍了這場戲,所以觀衆看到的是和56年前的辛德(dé)勒看到的是一樣的。
在這部黑白電(diàn)影裏把外套處理(lǐ)成紅色。你是怎麽考慮的?
老斯:那次大屠殺知道的人并不多(duō),隻在一些圈子裏秘密地流傳着。但是羅斯福和艾森豪威爾肯定知道。什麽東西都難以放慢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的清掃的腳步。協約國(guó)什麽也沒做,除了一直在打戰。這就是為(wèi)什麽我要讓那個鏡頭變成彩色的,就像小(xiǎo)女孩身上的外套那麽明顯。
《拯救大兵瑞恩》盡管是個悲劇,但沒有(yǒu)《辛德(dé)勒的名(míng)單》那麽壓抑。這部片的計劃是怎麽到你手裏的?
老斯:當時我想導二戰的題材,讀了很(hěn)多(duō)書、很(hěn)多(duō)劇本,還有(yǒu)很(hěn)多(duō)小(xiǎo)說。然後Robert Rodat的劇本通過中(zhōng)介送給我。其實這是幾十年來唯一一次我想拍中(zhōng)介送來的劇本。
你事先是怎麽計劃整部電(diàn)影的呢(ne)?
老斯:我一開始對于開場要怎麽拍并沒有(yǒu)什麽想法。我拍電(diàn)影都是連續着拍的,當然拍開場的戲也是連續着拍的,開場拍的是登陸奧馬哈海灘。拍這場戲的時候,過程很(hěn)意識流,我沒有(yǒu)用(yòng)故事闆,也沒有(yǒu)畫分(fēn)鏡,所有(yǒu)事情都是在腦袋裏完成的。所有(yǒu)我讀過的關于在諾曼底登陸幸存下來的故事,此時都發揮了作(zuò)用(yòng)。我當時沒有(yǒu)預料到26分(fēn)鍾的開場要花(huā)4周的時間才能(néng)完成。每次劇組人員過來問我:“下周我們應該就能(néng)拍完了吧?”我總是說:“我不知道。”正是因為(wèi)拍攝是即興的,所以我覺得電(diàn)影裏有(yǒu)給觀衆那種第一視角的沖擊感,因為(wèi)我當時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,就像一場真正的戰鬥。
有(yǒu)人評價《拯救大兵瑞恩》過于好萊塢化了,對此你怎麽看?
老斯: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戰争片,然後我有(yǒu)了拍現實主義戰争片的機會,而不是虛假的戰争片。實際上,我還克制了想要把它好萊塢化的沖動。批評的人們是因為(wèi)電(diàn)影裏有(yǒu)個布魯克林來的也有(yǒu)個猶太人,于是他(tā)們就會說:“噢,你用(yòng)的是Lewis Milestone在《白畫進攻》(A Walk in the Sun,1945)裏用(yòng)過的梗。你拿(ná)種族和文(wén)化的組合來顯示美國(guó)人是從世界各地來的。”這一點都不困擾我,因為(wèi)他(tā)們看過的二戰的電(diàn)影根本我沒我多(duō)。這些批評也不會對于《拯救大兵瑞恩》造成什麽影響。
你電(diàn)影的魅力一部分(fēn)來自于John Williams的配樂。你可(kě)以說說這個嗎?
老斯:John Williams對于我的電(diàn)影是貢獻最多(duō)的,我過去的電(diàn)影他(tā)隻有(yǒu)一部沒有(yǒu)幫我作(zuò)曲。他(tā)的貢獻是難以量化的,因為(wèi)音樂在你大腦做出反應之前就已經觸動了你的内心。在《E.T.》的結尾,ILM和我做出了自行車(chē)飛上天的效果,但其實真正能(néng)讓人感覺飄在空中(zhōng)的是John Williams,因為(wèi)他(tā)的小(xiǎo)提琴配樂實在讓人飄飄欲仙。觀衆随着弦樂越過了月亮,伴着他(tā)們着陸的也是John Williams的音樂。我覺得《E.T》的最後15分(fēn)鍾更像是歌劇,這要歸功于John Williams。不止這些,我之前的電(diàn)影,也都要感謝(xiè)他(tā)
你曾經說過,如果沒有(yǒu)拍《紫色》的經驗的話,你永遠(yuǎn)拍不出《辛德(dé)勒的名(míng)單》和《拯救大兵瑞恩》。具(jù)體(tǐ)是什麽意思呢(ne)?
老斯:縱觀我所有(yǒu)的電(diàn)影,《紫色》是我的成熟之作(zuò)。這是我的第一部非爆米花(huā)電(diàn)影。觀衆需要自行利用(yòng)他(tā)們的經驗和認知來理(lǐ)解這些角色。故事是從角色的台詞中(zhōng)表現的,而不是那種鲨魚襲擊避暑勝地或者車(chē)追車(chē)的大場面。我心裏清楚,盡管故事發生在美麗的鄉下,我想要表現出角色間的恐懼、想要在田園牧歌的畫面裏講述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。
你好像本來想把它拍成黑白的電(diàn)影?
老斯:我起初的想法是想把它拍成黑白,因為(wèi)其實我對自己并不怎麽自信,我怕自己把這個故事毀了,怕自己把它講得過分(fēn)花(huā)哨。如果用(yòng)黑白拍的話就不會顯得花(huā)哨了。我第一次退縮居然是為(wèi)了不想把電(diàn)影拍得太好看,後來攝影師換成了Allen Davieu,他(tā)和我還是決定把電(diàn)影拍的好看點,不管是臉部還是内外景都要好看,我覺得觀衆也許會記住電(diàn)影的美麗,以此蓋過原著那種暴力的詩意。
關于你的《幸福終點站》,這故事也有(yǒu)趣得很(hěn)。
老斯:這部片是對科(kē)波拉和雅克·塔蒂的緻敬。他(tā)在《于洛先生的假期》和《我的舅舅》的表演,表現了他(tā)的智慧,他(tā)善于用(yòng)他(tā)周圍的東西來使觀衆發笑。
我覺得《慕尼黑》跟你其他(tā)的電(diàn)影都不一樣。我沒有(yǒu)看到孩子啊或是其他(tā)你電(diàn)影的主題。盡管有(yǒu)恐怖主義,這部片是不是比較“未來主義”呢(ne)?
老斯:我從未覺得《慕尼黑》和我其他(tā)的電(diàn)影有(yǒu)什麽不同,我更想把它看成一個應該被知道的故事,而那時候我覺得是時候拍它了。它滿足了我去探讨嚴肅事務(wù)的需求,我支持以色列,我想通過這種真誠的非暴力的方式來支持那個區(qū)域的和平。
你有(yǒu)預料這部電(diàn)影會引起這樣的争論嗎?
老斯:我知道《慕尼黑》是我政治性最強的電(diàn)影。我們在拍的時候,我和Tony Kushner有(yǒu)時候會坐(zuò)在一起讨論人們會如何理(lǐ)解這部電(diàn)影。他(tā)甚至說:“這部電(diàn)影會引起很(hěn)多(duō)罵聲,這肯定不會是好事。”我就說:“如果會有(yǒu)什麽好事發生呢(ne)?”他(tā)說:“這可(kě)能(néng)要等到10年之後才會有(yǒu)吧。現在上映的話,肯定不是這樣的。”
除去政治性的東西,這部電(diàn)影讓我覺得好看的還有(yǒu)就是,這是一部一流的驚悚片。
老斯:我當時想到的是Fred Zinneman的《豺狼的日子》(Day of the Jackal,1973),和Costa-Gavras的《獨家新(xīn)聞》(Z,1969)和Pontecorvo的《阿爾及爾之戰》(The Battle of Algiers,1966)。我在處理(lǐ)驚悚部分(fēn)的時候,這些電(diàn)影一直在我腦子裏面。
在《A.I.》裏,哪些東西是你的,哪些是庫布裏克的?
老斯:人們所推測和事實相反。人們都覺得庫布裏克會在David和Teddy沉入海底那裏結束電(diàn)影。而我呢(ne)因為(wèi)把2000年後的故事放到電(diàn)影裏而飽受批評,他(tā)們覺得我這樣毀掉了庫布裏克的電(diàn)影。其實這個電(diàn)影版本都是按着庫布裏克95頁(yè)的大綱來的。 《A.I.》的關鍵部分(fēn)都是庫布裏克的,我隻是盡可(kě)能(néng)地人道地來接近他(tā)的視角。
你有(yǒu)跟他(tā)讨論過這個電(diàn)影嗎?
老斯:我們在電(diàn)話上讨論過幾個小(xiǎo)時。在80年代的時候,庫布裏克說過:“應該你來拍這部片,而不是我,這是你更會表達的情感,我不擅長(cháng)。”他(tā)講過幾十次。庫布裏克唯一一次積極地讓我參與的電(diàn)影就是《A.I.》。第一次他(tā)說:“我想讓你讀讀我寫的大綱。”在這之前,我們認識也算挺久的了,他(tā)也沒給我寄過什麽大綱。
《少數派報告》是在9·11之後上映的,講的是未來世界的故事,還提出了對自由意志(zhì)的疑問。是什麽讓你想拍這部電(diàn)影的呢(ne)?
老斯:我一直以來都想拍一部喬治·奧威爾式的電(diàn)影,因為(wèi)我年輕的時候很(hěn)喜歡《1984》。後來《少數派報告》的劇本出來了,是John Cohen和Scott Frank先後寫的劇本。我們寫了很(hěn)久。我們計劃拍成鮑嘉/白考兒式的黑色偵探片。除去政治性的因素,它模仿了《逃亡》(To Have or Have Not,1944)和《馬其他(tā)之鷹》(The Maltese Falcon,1941)。對我來說這是一部雜糅的電(diàn)影,它表達了我對黑色電(diàn)影的熱愛,還有(yǒu)對那種老式“神秘謀殺案”片的熱愛。
我們是用(yòng)Super 35拍的,這意味着在發行的拷貝裏要放大一點,這樣效果會更真實。電(diàn)影的畫面的優點都要感謝(xiè)攝影師Janusz Kaminsk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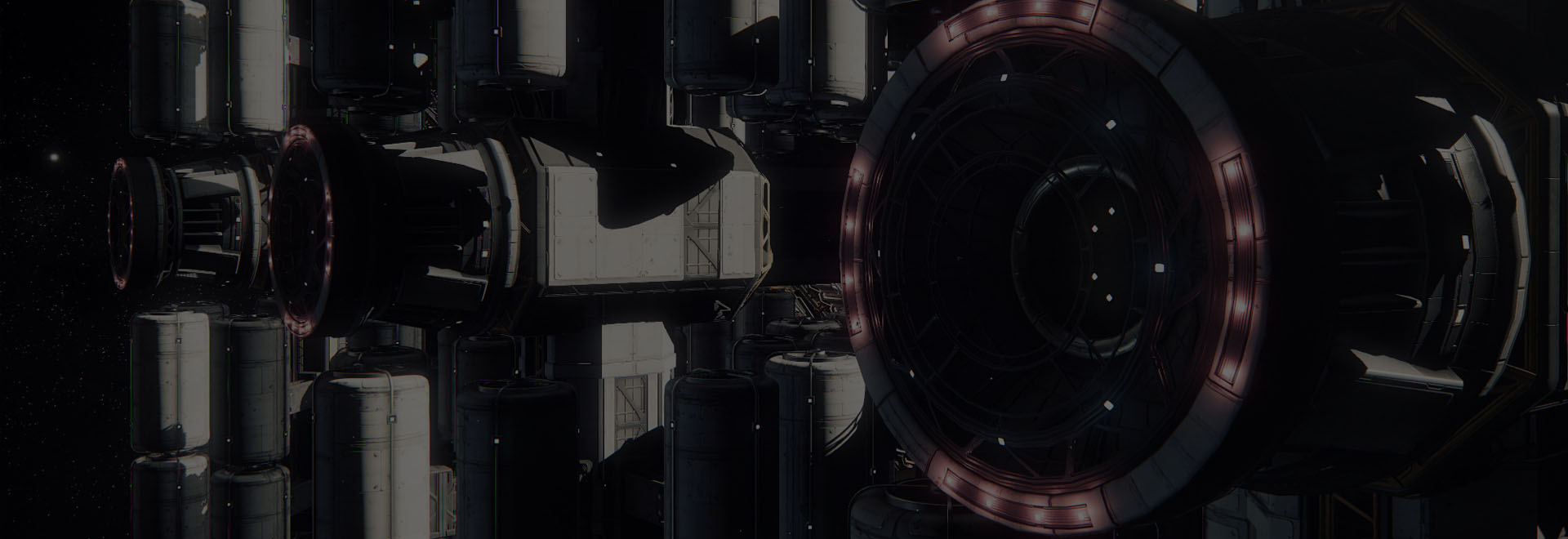


 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
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