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所營造和勾勒出的詩意,以及對于時間和空間、回憶與夢、潛意識的思索,令人感到意味深長(cháng)…如同詩歌一樣無法具(jù)體(tǐ)描述,但這種感覺的産(chǎn)生,不隻來自故事,更是形式和内容的共同探索。所以,如果追回到源頭,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在劇本之初如何去把握這一切?
影視工(gōng)業網直播欄目【劇組有(yǒu)料】請到了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劇組主創,聲音、攝影、美術...為(wèi)我們分(fēn)享了這部電(diàn)影的制作(zuò)過程和理(lǐ)念。下載幕後英雄APP,查看全部回放。
本期分(fēn)享的内容來自劇本顧問張大春老師,為(wèi)我們解構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的創作(zuò)過程,以及對于形式和文(wén)字上的解讀。張大春老師說,畢贛驚人的才華是在以影像為(wèi)筆(bǐ),通過對空間角度,時間、結構的精(jīng)準把握,在大銀幕上呈現出讓人耳目一新(xīn)的視聽體(tǐ)驗。
文(wén)章隻整理(lǐ)了部分(fēn)直播内容,如果想要觀看完整對談,歡迎下載幕後英雄APP回看。
張大春老師
影視工(gōng)業網:您作(zuò)為(wèi)文(wén)學(xué)顧問如何具(jù)體(tǐ)切入一部電(diàn)影的工(gōng)作(zuò)中(zhōng)?在《一代宗師》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中(zhōng)具(jù)體(tǐ)的工(gōng)作(zuò)方式是怎樣的?
張大春:是因為(wèi)“編劇”本身的需要,每個片子不一樣。在30年前,導演胡金铨他(tā)找到我,要我做編劇,我們兩個合作(zuò)了兩個劇本,但是都沒有(yǒu)拍成。在這樣的過程中(zhōng),我跟着胡導演學(xué)了很(hěn)多(duō)東西。當然,這個經驗仍然屬于編劇的範疇,我也是因為(wèi)這兩次的挫折,發誓不做編劇。但是因為(wèi)我很(hěn)多(duō)朋友就在這個圈子中(zhōng),他(tā)們有(yǒu)時候希望我去幫忙處理(lǐ)其他(tā)人的作(zuò)品,所以才有(yǒu)了這個身份。
其實王家衛根本不需要編劇,他(tā)自己就是作(zuò)品中(zhōng)最核心的編劇。但是他(tā)每一部片子都一定都會雇請一位或幾位編劇幫他(tā)把故事做整理(lǐ)。所以我也非常清楚,我參與王家衛電(diàn)影的工(gōng)作(zuò),隻能(néng)夠成為(wèi)他(tā)訴說的對象,或者我在他(tā)訴說故事的過程中(zhōng),提供一些反饋。換言之,他(tā)需要一個聊天的人,但這和形成故事,或是做細膩的編劇是兩回事。更像打乒乓球,你發球過來,我打回去,就是想盡辦(bàn)法接住他(tā)的球,并且喂回給他(tā),讓他(tā)能(néng)夠再有(yǒu)揮拍的空間。但對我個人來說,這個創作(zuò)過程是沒有(yǒu)意思的,因為(wèi)它不是我的作(zuò)品,我隻是提供服務(wù),然後提供某一些他(tā)可(kě)能(néng)需要的信息,在這之中(zhōng)沒有(yǒu)我的創作(zuò)。
老實說,在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我作(zuò)為(wèi)一個所謂的文(wén)學(xué)顧問很(hěn)慚愧,我仍然就像拳擊手準備比賽之前的練習師,拿(ná)着兩個大闆在擋畢贛的拳。我在和王家衛的合作(zuò)上可(kě)能(néng)還寫了很(hěn)多(duō)内容,比如說我們有(yǒu)通一百多(duō)封電(diàn)郵,至少在電(diàn)郵裏是發生了很(hěn)多(duō)戲,有(yǒu)了很(hěn)多(duō)所謂的編劇工(gōng)作(zuò)。但是在畢贛這邊,他(tā)隻是開拍之前來到台北來,我們應該有(yǒu)五天的時間不斷的把故事你講一句我講一句。但多(duō)半我還是像一個帶護具(jù)的練習師,所以整個故事仍然是導演自己既是導演又(yòu)是編劇來完整創作(zuò)的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我理(lǐ)解您的意思是,您認為(wèi)文(wén)字或者文(wén)學(xué)在對影像的幫助上不是很(hěn)直接,無法可(kě)以給到一些很(hěn)具(jù)體(tǐ)的描述或感受?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創作(zuò)起點是文(wén)字嗎?
張大春:這要看導演和文(wén)學(xué)顧問或者編劇彼此之間的默契以及信任。畢贛他(tā)常常會根據一個影像所發展出來的某一個情節因素,去找到跟它完全無關的情節,去看有(yǒu)沒有(yǒu)一個遙遠(yuǎn)的紐帶可(kě)以聯系起來。所以有(yǒu)些作(zuò)品就會顯得不是那麽方便、直接的解釋。而喜歡畢贛的觀衆,也就在這個時候就會認為(wèi)具(jù)有(yǒu)挑戰性。
比如像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黃覺扮演的這個角色,他(tā)進入到戲院之前是在處理(lǐ)他(tā)的記憶,進入到醫(yī)院,觀衆戴上3D眼鏡後已經來到了夢境。換言之,畢贛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,記憶之不足,以夢境來補充。不然這電(diàn)影為(wèi)什麽要有(yǒu)一百多(duō)分(fēn)鍾?它前面2D的内容是回憶,是不斷的去想,而且還要去修正、去詢問我那時候是怎樣的。他(tā)想要建構起自己過去生命中(zhōng)迷失了的片斷,可(kě)是不成功,所以後面靠一個單一鏡頭完成,那就是一個夢。
夢是一個鏡頭嗎?正好反過來,在我們的人生醒着的過程,我們是不剪片的,人的意識流是不會斷的。回頭看畢贛的電(diàn)影,人清醒時的記憶應該是像河流一樣不斷,但是它卻是碎片化的,是經過剪接處理(lǐ)過的影像。而夢應該是破碎的,而且是彼此之間邏輯不清晰的,他(tā)反而用(yòng)一個鏡頭去解決。這兩個對立起來,也就是說,他(tā)用(yòng)夢的手段來處理(lǐ)一個記憶,用(yòng)意識的手段去處理(lǐ)了夢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大家總是會講到文(wén)學(xué)和影像之間的關系,以及互相之間能(néng)夠起到什麽作(zuò)用(yòng)。因為(wèi)您之前在做文(wén)學(xué)顧問,是和影像以及文(wén)字都有(yǒu)接觸的。您覺得文(wén)字和影像之間怎麽樣才能(néng)更好的協作(zuò)?
張大春:我們從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來做一個例子,從畢贛的《金剛經》和《路邊野餐》這一部短片一部長(cháng)片就可(kě)以看出來,他(tā)有(yǒu)一些非常獨特的企圖。這個企圖啓發自一個明确的視覺影像。他(tā)要完成這個影像之餘,不能(néng)隻有(yǒu)一個影畫或者影像,也就是說他(tā)不能(néng)隻有(yǒu)這一組鏡頭。他(tā)把拍攝的動力很(hěn)強,所以他(tā)隻好再外包,包成第一個故事,包成第二個故事。
第一個故事《金剛經》,他(tā)一定有(yǒu)一個非常核心的意象,他(tā)必須把它完成,所以他(tā)用(yòng)故事來包它。《路邊野餐》也是如此。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開片的第一個鏡頭,就是畢贛在創作(zuò)過程之中(zhōng)的一個核心的鏡頭,這個鏡頭發展出來,就變成了後來的故事。但是這個故事又(yòu)牽扯到畢贛這三部片子都有(yǒu)一種文(wén)學(xué)上面的追問,文(wén)學(xué)作(zuò)者永遠(yuǎn)會追問說,我為(wèi)什麽要這樣做,我怎麽會走到這一步,我的人生怎麽回事。他(tā)的作(zuò)品一部比一部更往内在去尋找說人的處境、地位,人的情感來曆,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最明确的就是這一點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所以,不能(néng)說電(diàn)影或者導演依賴于文(wén)學(xué),而是依賴于他(tā)創作(zuò)之初的那個動力,那個感覺?
張大春:對,好萊塢沒有(yǒu)所謂的什麽文(wén)學(xué)電(diàn)影導演,但是有(yǒu)作(zuò)者電(diàn)影或者是風格電(diàn)影。什麽是作(zuò)者呢(ne)?在台灣來講,像侯孝賢、楊德(dé)昌大概就是。我相信在大陸第五代的導演也帶來了某一些非常強大的刺激,張藝謀、陳凱歌、田壯壯那一代。那他(tā)們之後一定會想到幾個名(míng)詞,比如賈樟柯。他(tā)們中(zhōng)有(yǒu)些在市場上有(yǒu)更多(duō)的成就,有(yǒu)一些在于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像風格,或者說在講故事的方法上建立了自己的地位。所以它是兩套,但是我們不能(néng)說,哪些是文(wén)學(xué),或者冠名(míng)說他(tā)是文(wén)學(xué)。反而我們是可(kě)以知道,以作(zuò)者論為(wèi)核心的導演,或者說以風格為(wèi)核心的電(diàn)影導演,他(tā)對于市場上的呼喚不是那麽在意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那您怎麽看形式和内容的結合?
張大春:有(yǒu)比較世故一點的導演,會把他(tā)的表現形式和所處理(lǐ)的故事題材做一個對接。也就是說他(tā)一定要替某一個題材找到唯一适合、而且充分(fēn)表現的形式。有(yǒu)的導演是悶頭拍,就是把腦子裏出現的影像拍出來,這樣不一定能(néng)成功。如果他(tā)足夠真誠的去反省視覺的基礎元素,可(kě)能(néng)會打動和他(tā)一樣的人。當他(tā)故事又(yòu)是一個多(duō)數人可(kě)以接受的故事時,片子可(kě)能(néng)會變成一個現象極的産(chǎn)品。
但我要說的是第一種導演,他(tā)就和其他(tā)藝術家一樣,他(tā)們更多(duō)的是希望在他(tā)的專業領域中(zhōng),找到一個不可(kě)被替代的形式,去表現一個不可(kě)被替代的題材。人想題材不容易,比如說所有(yǒu)的作(zuò)品幾乎都逃脫不開戰争、愛情、死亡這三大主題。那麽如何表現戰争,如何表現愛情,如何表現死亡,創作(zuò)者要有(yǒu)自己的方向吧?那如何表現是什麽樣的戰争,什麽樣的愛情,什麽樣的死亡,創作(zuò)者必須再去參謀。所以它更分(fēn)化的去針對創作(zuò)者要表現的題材,找到了相應、而且是唯一的技(jì )巧,要做到這個,不但要有(yǒu)這種熱忱、動機,還要有(yǒu)這個能(néng)力,這是非常難得的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提到《路邊野餐》它會給人一種詩意的感覺,沒有(yǒu)辦(bàn)法用(yòng)語言或文(wén)字去具(jù)體(tǐ)的形容它。您怎麽理(lǐ)解這種電(diàn)影的詩意表達?
張大春:你剛剛提到的一個關健詞:詩意。詩意英文(wén)是Poetic,很(hěn)像詩一樣。我舉一個例子,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,低頭思故鄉。”所有(yǒu)的中(zhōng)國(guó)人都知道這首詩,但隻要把這20個字翻譯成白話文(wén)或口語,就不是詩了,所以它是不可(kě)以被翻譯的,這就是看到《路邊野餐》的感受。觀衆可(kě)以感受到一種美,或者感受到一種獨特的表達形式。但是它不能(néng)用(yòng)另外一種表達形式來取代,也似乎不能(néng)被解釋。它為(wèi)什麽那麽吸引我。“一個舉頭,一個低頭”而已嘛。人人都能(néng)說,但是就你沒說出來,他(tā)說出來了。畢贛會給人一種,所謂的詩意,多(duō)多(duō)少少和這個有(yǒu)關,就是它不可(kě)被傳譯,不可(kě)被翻譯,不可(kě)被解釋。
影視工(gōng)業網:我之間看到一個采訪,您自己說如果不寫小(xiǎo)說,會去做剪輯師?所以您怎麽看待《地球最後的夜晚》的結構?
張大春:我非常羨慕剪輯師,剪輯師有(yǒu)一種結構能(néng)力。我認為(wèi)剪輯師是一個代名(míng)詞,他(tā)是結構關系的創作(zuò)者。結構元素彼此的支援,是一種極緻的美。包括我現在寫毛筆(bǐ)字,絕對不是每個字一樣大,一樣黑,一樣圓。而是參差錯落,筆(bǐ)劃照應,幾乎可(kě)以說沒有(yǒu)一筆(bǐ)沒有(yǒu)它的來曆,而那個來曆也恰恰就是結構的一部分(fēn)。我的意思就是說,結構是無所不在的,隻是看你怎麽去尋找和品味,有(yǒu)的時候是看創作(zuò)者怎麽去架構它。
畢贛很(hěn)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(tā)總能(néng)夠讓所有(yǒu)元素在不同的情節、地位去找到彼此聯系和呼應的關系,也就是所謂的結構,他(tā)可(kě)以用(yòng)旁白裏的詩句,有(yǒu)的時候是一個單純的空景,有(yǒu)的時候是角色之間相互不經意的對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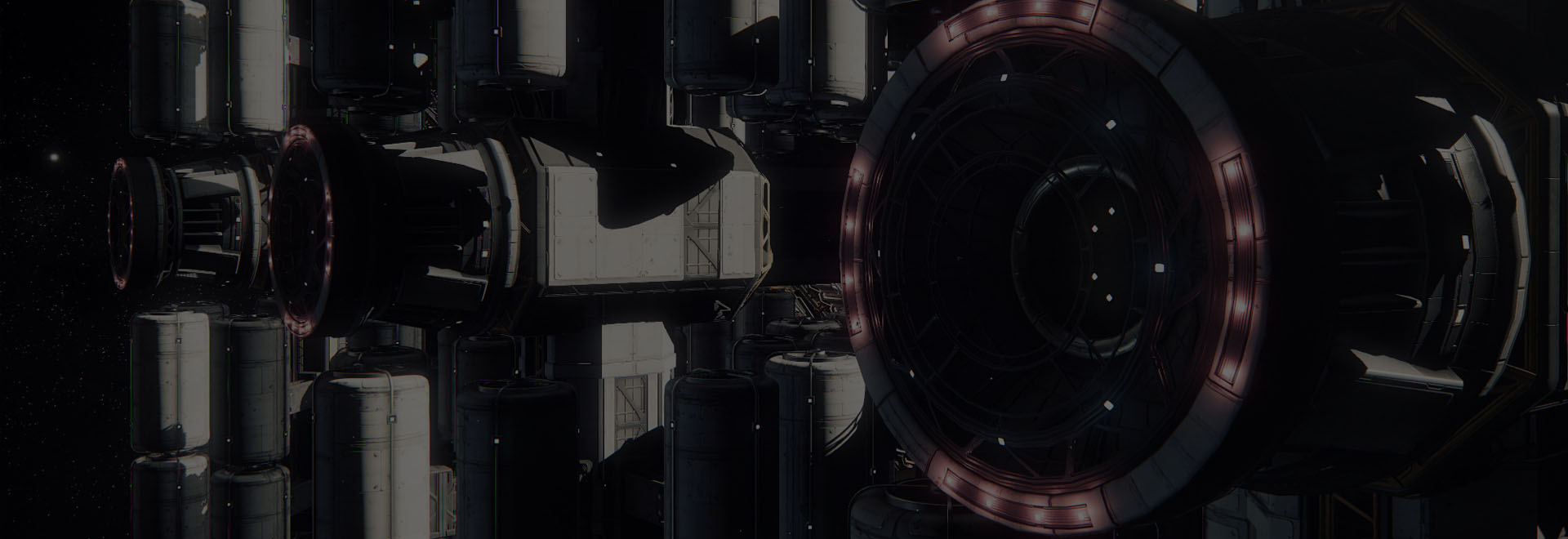


 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
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