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有(yǒu)些同學(xué)就說希望聊一些具(jù)體(tǐ)的,那我們可(kě)以放一些片斷,比如像場面調度。你們隻要看過《海上花(huā)》的話,那是我第一次用(yòng)軌道拍長(cháng)鏡頭,就是跟李屏賓合作(zuò)的第一次,用(yòng)長(cháng)鏡頭呈現的。為(wèi)什麽要談這個所謂的長(cháng)鏡頭跟場面調度呢(ne)?基本上因為(wèi)人們一般對固定的鏡頭擺在那邊已經很(hěn)煩了,你說長(cháng)鏡頭,我就每天一定要長(cháng)鏡頭,每天用(yòng),用(yòng)久了不是很(hěn)煩嗎?那就開始擺軌道移動,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你們看《海上花(huā)》第一場,這個沈小(xiǎo)紅,出場的這一場,這是絕對的安(ān)排,但是我喜歡這樣,它的移動不是為(wèi)移動而移動,你們可(kě)以感覺得出來。

吃飯這個長(cháng)鏡頭,7分(fēn)鍾。從沈小(xiǎo)紅的字幕開始。哇,真長(cháng),一個鏡頭。這是她的第一場出場,接下來她斷斷續續地會有(yǒu)第5場或者是第7場什麽,次序是這樣子的。我拍攝的方式是從第一場開始拍,第1天拍一場,可(kě)能(néng)拍很(hěn)多(duō)take(條),第2天再拍可(kě)能(néng)下一場,他(tā)們的下一場,然後可(kě)能(néng)也是拍很(hěn)多(duō)take。假使有(yǒu)5場戲,照順序,用(yòng)5天拍,然後回頭再從第一場再拍5天,有(yǒu)的拍了三次,有(yǒu)的還拍了第四次,每一天都拍好多(duō)take(條)。為(wèi)什麽呢(ne)?這等于是用(yòng)底片rehearsal(走戲/排練)。用(yòng)底片rehearsal有(yǒu)一個好處,正式嘛,演員都全力以赴,剛開始拍,第1天的時候根本不行,那個氛圍根本出不來,運動也運動得不行,都是慢慢調整出來的。
《海上花(huā)》裏有(yǒu)一個日本演員,她在現場是講日本話的,那我就把她的字句跟我的對白的字句對得剛剛好,這個日本演員不習慣這種長(cháng)鏡頭,她的話講完了她就不知道在那邊該幹嗎了。她每次拍完一個take(條),就問翻譯,導演怎麽講,那個翻譯說:導演沒有(yǒu)講。她一直問,到拍第二輪她還在問,不過之後她就不問了。她明白,我也沒說什麽,我從來沒有(yǒu)教她,她希望得到一個sign(信号),然後她可(kě)以按照那個指示演。希望我提示她,她馬上可(kě)以用(yòng)。但是我要她投入,所以我統統不講。到第三輪的時候,她知道她要面對她自己了。這個演員以前是拍短鏡頭形式的,她本來是松竹公(gōng)司,很(hěn)少出去演,後來她拍過《海上花(huā)》之後,她就開始在日本其他(tā)的電(diàn)影上演了非常多(duō)的戲,是從《海上花(huā)》這個訓練開始的,我感覺。所以基本上是要拍三次,才能(néng)成熟到一個氛圍,才有(yǒu)一種氣氛,這種氣氛就像我們看到的"長(cháng)三書寓"生态。你看那個移動,從沈小(xiǎo)紅開始,旁邊那個傭人,是走過去拿(ná)茶葉的,這是一個sign(信号),她是在邊上,你要移動的時候才能(néng)看到她。她變成一個動機,就是你畫面裏有(yǒu)個東西在移動,跟着她移動。通常我會盡量避免演員走動,你跟着她拍,所以我叫阿金——娘姨底下那個小(xiǎo)娘姨,就是叫她什麽時間去拿(ná)什麽,送水的什麽時候來,那這些通常都是sign(信号),是配合對白的,所以要pan(搖鏡頭/搖攝)到沈小(xiǎo)紅的時候,娘姨走到茶櫃去拿(ná)茶葉的時候,pan到沈小(xiǎo)紅講話,因為(wèi)你這樣會比較不自覺地。不然的話,你這樣橫pan(橫搖),這個人講話pan到那個人講話,觀衆有(yǒu)時候會醒的。有(yǒu)時候有(yǒu)對白還好,沒對白會醒。而且我感覺也不自然。有(yǒu)時候你跟着演員,她走哪裏你跟到哪裏,也太僵硬了。所以這個是拍了好幾次,我跟攝影師一直調整。

我最早當副導演的時候,第一個劇本,一條街(jiē)道,我記得是《桃花(huā)女鬥周公(gōng)》,元雜劇改編的。那是古裝(zhuāng),我當副導演,我去把《清明上河圖》上面所有(yǒu)的細節弄清楚,圈出幾個來,叫道具(jù)做,棚子什麽做好,然後研究裏面的人物(wù)造型,找了很(hěn)多(duō)臨時演員來,然後我在現場調度是怎麽調度,就是我喊camera開始之後,裏面這些人一個或者是兩三個聽到camera之後數30秒(miǎo)後開始,在那裏停留再走到那裏,那邊那個人是看到這個人走到這裏,然後你開始去那裏,那邊是怎麽樣,完全是調度,不會喊的。隻要一個指令,他(tā)們就遵照這種方式走,然後我叫他(tā)們走一遍,一看,某些地方人太重複了,或者太擠,或者太空,我再重新(xīn)調度,不需要在那邊用(yòng)walky-talky(對講機)。以前我們在現場是不收音的,"那個某某走"——聽不到——"走"(很(hěn)大一聲)。其實這邊還是會被影響,其實這邊"hello,hello,hello……還不出來",這種方式根本不需要,而且你可(kě)以冷靜地看他(tā)們走,這樣子行動對不對。通常是在古裝(zhuāng)戲,街(jiē)道上需要這麽安(ān)排的。
拍時裝(zhuāng),在現代背景,或者是以前的背景,假如說是實景,我在拍《悲情城市》的時候,就是醫(yī)院那一區(qū),附近的居民(mín)就是我的臨時演員,全部給他(tā)們談好。為(wèi)什麽?假如叫一個台北的臨時演員去那邊,他(tā)們恐怕連走路都不會走。因為(wèi)他(tā)對那個地方不熟悉,所以走的時候很(hěn)怪,但是換作(zuò)當地的人,拿(ná)一個東西在那邊晃啊晃啊,絕對就是跟那個地方match(相配)的,完全是合的。這些其實都是細節,你無時無刻都必須注意,才能(néng)做到一個真實的氛圍。我常常是這種,像《悲情城市》中(zhōng)送葬的隊伍,其實是我拍的時候他(tā)們正好送葬,我問他(tā)們可(kě)不可(kě)以再來一回,他(tā)們說可(kě)以,隻要付錢。錢談好了,再來一回,我就拍了。時常是這樣子,因為(wèi)有(yǒu)時候這些東西你要再跟他(tā)們聯絡,會很(hěn)慢,而且有(yǒu)時候你要是看不到,就沒想到。你看到了還不用(yòng)?那一定要用(yòng)的。這種情況太多(duō)了。有(yǒu)時候我們在拍戲,比如說拍一群人的反應,正好那群人在那邊很(hěn)過瘾的樣子,我們在這邊偷偷地把鏡頭對着他(tā)們,用(yòng)銳角。銳角你們知道,就像zoom(推)上去就是銳角,廣角之外就是銳角,基本上可(kě)以壓縮的,然後我們這些人全部看這邊,鏡頭是對這邊,然後鏡頭還擋着,隻剩下一個頭看着,那邊還出什麽聲音,然後他(tā)們就這樣一直看着。像《冬冬的假期》我記得有(yǒu)一場是他(tā)們抓麻雀回來要不就是小(xiǎo)孩回來,有(yǒu)一群人在看,基本上就是用(yòng)這種方式。很(hěn)多(duō)常常會用(yòng),一看那個人很(hěn)過瘾,需要我馬上就會拍。《戀戀風塵》那麽多(duō)雲在走,氣候的變化,那個不是去等的,如果要等要等死的,越等就越等不到,我們是在拍戲中(zhōng),突然看到便趕快拍下來。或者是外面正在下雨,我們正在拍這場,我腦子馬上轉,下雨這個要怎麽用(yòng),馬上就調一場去拍,然後你再前後再連。
所以場面調度基本上還是有(yǒu)個原則,這個原則就是怎麽樣看上去很(hěn)真實,看起來不會像安(ān)排的樣子,這是個原則,這個原則通常是要靠長(cháng)時間的累積跟曆練才有(yǒu)。你看《桃花(huā)女鬥周公(gōng)》,我是第三個片子當副導,很(hěn)自然,我就是用(yòng)這種方法。所以我現場隻有(yǒu)一個助導,是個女的。很(hěn)多(duō)時候你要看現場的狀況調度。很(hěn)多(duō)時候我拍車(chē)站,都是這樣。

場面調度通常是有(yǒu)個sign(信号),那個演員過來,另一個過去……比如《南國(guó)再見,南國(guó)》他(tā)們在打紙牌的時候。那個鏡頭就是從打紙牌一直到有(yǒu)個人來找高捷,然後高捷就把牌交給另外一個人打,他(tā)自己就過去跟那個人講話,林強在那邊打彈子,大哥(gē)大響了林強就過去接。因為(wèi)以前大哥(gē)大都是集中(zhōng)放在一個地方,因為(wèi)隻有(yǒu)那個地方才收得到,林強接了電(diàn)話後再交給高捷,高捷後來跟人談的時候,喜祥又(yòu)進來,這一段也是蠻長(cháng)的一個調度。這個環境基本上是一邊可(kě)以休息喝(hē)咖啡的地方,另一邊主要是彈子房。《南國(guó)再見,南國(guó)》差不多(duō)是十幾年前,那時候去内地是一個夢,很(hěn)多(duō)人去。當然也有(yǒu)很(hěn)多(duō)人失敗,能(néng)夠撐住的不多(duō)。這是早期的時候。然後演那個人,那個人是個刑警,我真是找了一個刑警來演,本身是一個刑警,刑警才有(yǒu)這種味道,因為(wèi)曆練過,不然普通的熟人是演不來的,他(tā)的感覺又(yòu)非常對,油,很(hěn)懂,很(hěn)會說,所以找他(tā)來演。基本上這裏有(yǒu)好幾件事,一開始,因為(wèi)他(tā)們電(diàn)話都集中(zhōng)在那邊,有(yǒu)人來接,後來那個人就來了,來了進去之後就看見高捷在那邊打牌,他(tā)就交給他(tā)旁邊的小(xiǎo)弟(dì)打,他(tā)就自己去處理(lǐ)。處理(lǐ)時講了半天,他(tā)說不可(kě)能(néng),他(tā)大哥(gē)會盯的,電(diàn)話響,林強去接那個電(diàn)話,交給小(xiǎo)高,小(xiǎo)高講了後面要發生的事情,就是小(xiǎo)麻花(huā)出狀況了。然後他(tā)到那邊去接,這時候喜祥進來。喜祥帶了一個人進來。這邊在講這個,那邊在講那個。這個其實是很(hěn)繁複的兩件事情的場面調度。因為(wèi)通常我拍片都喜歡這樣,我不喜歡單獨的一個。不過盡管這樣子講了,好像聽了也沒有(yǒu)什麽,場面調度完全是看現場狀況在執行的,每一次每一個現場都會有(yǒu)個味道要你去掌握,而且那邊的生态跟生活軌迹你自己要很(hěn)清楚。這種是已經習慣了的。看起來很(hěn)簡單,我知道要做到不是那麽容易的,可(kě)能(néng)需要拍好幾個take(條)才能(néng)拍到。類似這種,你們在我的電(diàn)影裏應該都能(néng)常常看得到,從《風櫃來的人》以後,一直有(yǒu)這種。

《風櫃來的人》裏面有(yǒu)一場砸磚頭的。他(tā)們在那邊賭博,鈕承澤在那邊跟人家打架,然後他(tā)不是跑出鏡頭,其實是違背了方向,從鏡頭左邊出去,從右邊進來,這個在一般的鏡頭上imageline(軸)是違背的,但是我感覺一點關系都沒有(yǒu),開心得很(hěn),你們等會看一下。鈕承澤從右邊出去,從左邊進來的,這個連接的是我以前拿(ná)磚頭砸人的一個記憶。因為(wèi)我感覺那個磚頭真的很(hěn)猛,很(hěn)強的暴力感,很(hěn)暴。那個時候我記得是在東亞戲院,我們三個人出來,碰到黃埔新(xīn)村裏面的一個男的,因為(wèi)有(yǒu)仇,鈕承澤一下就抓了一個鋤頭,牆壁旁邊放了一個鋤頭。我那個朋友就抓了一個竹竿,他(tā)們兩個一上去就對打。那個竹竿一下子就碎掉了,放在旁邊太久了,黑了,一下子就碎掉了,碎了他(tā)就往回走。我就拿(ná)了個磚頭,我看那個人過來,我就"砰"砸向他(tā),就看他(tā)消失在我的視線(xiàn)裏。那個印象非常深,所以我在電(diàn)影裏就用(yòng)了這個。戲裏面的磚頭并不真,是用(yòng)泥漿做的,隻是做成磚的樣子,加一點重的感覺。這個片子在夏威夷影展,那時候第一次出國(guó)他(tā)們放這個片子,全場在看,看到這個,全場的觀衆就"啊"。後面有(yǒu)鈕承澤去找景和的家,他(tā)嫂嫂在外面殺魚,很(hěn)多(duō)蒼蠅,然後看他(tā)拿(ná)鋤頭出來,他(tā)朋友不是被打了?他(tā)要去找。我那個時候在那邊的感覺就是,那些觀衆看我們就是一種蠻荒之地的野蠻人。我感覺以他(tā)們的角度可(kě)能(néng)會有(yǒu)這種感覺。然後更奇怪的就是整個電(diàn)影配的是他(tā)們非常熟悉的像國(guó)歌一樣的《四季》,是楊德(dé)昌幫我配的。那個片子拍完我本來是找李宗盛做的歌配好,楊德(dé)昌看完後說,我幫你重配。已經上片了,我又(yòu)再重新(xīn)finalmixing(最後混錄)。我說:ok(好),所以他(tā)重新(xīn)幫我找了《四季》配,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這版是楊德(dé)昌配的音樂。以前我對交響樂完全沒有(yǒu)感覺,但因為(wèi)《四季》。我後來非常喜歡《四季》,因為(wèi)那個時間感非常強地凝聚在音樂裏面。《四季》你們知道呵?比如說他(tā)們幾個在海灘那場,放那個音樂,那是一種寂寞,生命的本質(zhì)的一種能(néng)量,它反而有(yǒu)一種寂寞,我自己看楊德(dé)昌配的《四季》實在是非常過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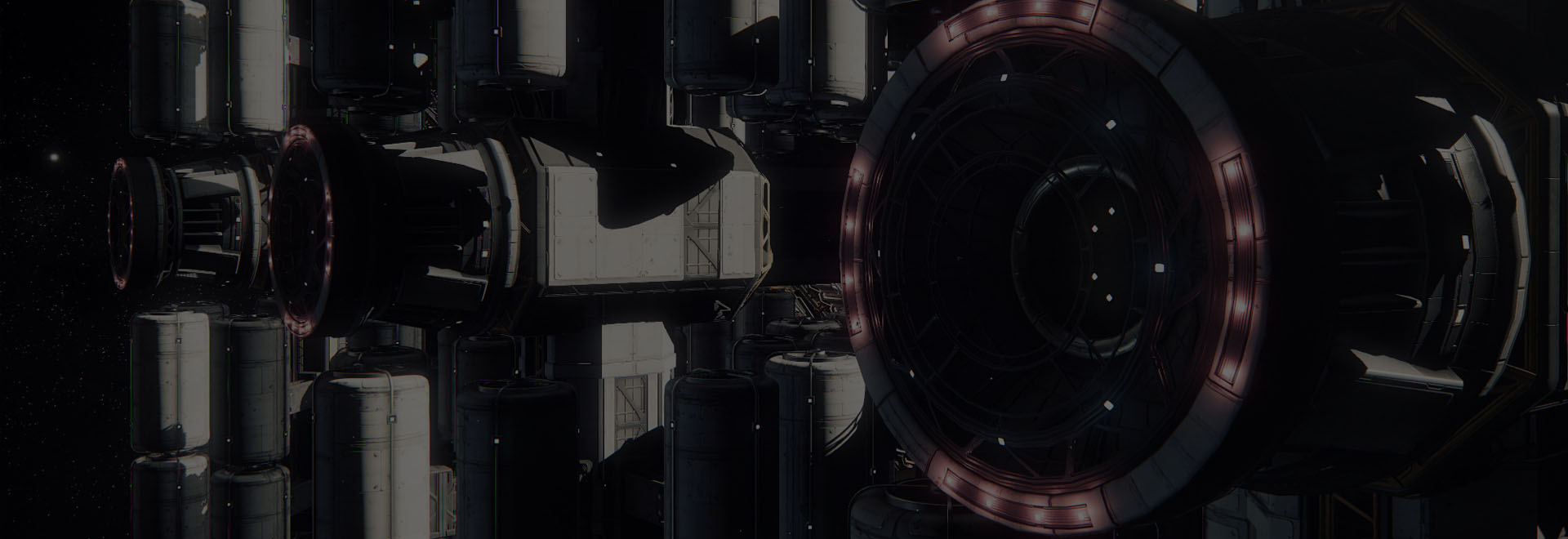


 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
歡迎關注博為(wèi)微信公(gōng)衆号